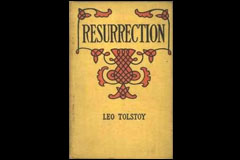喝酒
小時候,家裏很窮,一年的糧食不夠半年吃,父親雖然愛喝酒,但沒有糧食,只能等到街天去離家很遠的集市,用兩毛錢買二兩老白乾解酒癮。父親每次站在小店的酒櫃前,例行公事一樣地買酒,老闆還來不及補錢,他卻已把二兩老白乾沖到肚子裏面。生產隊裏為了解決許多男勞動力的喝酒問題,請來了外地的釀酒師傅,用乾蔗渣作原料釀造白酒。當然,就是乾蔗渣這樣的原料也不是很多,所以,乾蔗渣酒還得按工分分配,我記得我家一年分到這樣的酒30公斤左右。
乾蔗渣酒不好喝,苦裏含澀,甜味不足酸卻有餘,可是一到父親口裏,就變成了玉液瓊漿。坐在火塘邊的木凳上,茶在罐裏泛起清香,而溫過的乾蔗渣酒散發出來的香味,飄得更遠。這樣的夜晚,鄰居就不請自到,一同與父親圍着火塘談着玉米地裏的鼠災,水稻田裏的病害,當然最終的落腳點是溫着的那碗乾蔗渣酒上,吃酒人不小器,父親也一樣,即便明天還得跑到街上買酒,今晚絕對不會藏下半滴。
看多了父親酒後那份滿足狀,品酒那份陶醉樣,還上小學的我,在一次放學後稱父親母親都不在家,就偷偷地倒了一碗,也像父親一樣把酒溫到火塘邊,妹妹也跟着我蹲在一邊,看着酒花在微火中泛起,學着父親把溫了的酒倒在小杯子裏,我和妹妹都喝了一小口,不料乾蔗渣酒也會醉人,不是父親說“酸巴巴的不力”那樣,才兩口下肚,妹妹就醉得躺到了床上,而我卻越喝越有勁,竟把滿滿一碗乾蔗渣酒喝到胃裏。父親回來後,看到他的酒少了許多,還以為是盛酒的瓶子有問題,左看右看之後,才到我面前走了一圈,實際上一圈還沒有走完,父親就揪住我的耳朵,“酒是不是你偷喝的?”
我不承認不行,口裏呼出的都是酒味。再看看妹妹還睡在床上,還是因為酒惹的禍,父親狠狠地揍了我一頓,還讓我撕下一頁作業本紙,寫出滿滿一篇保證書,偷喝酒的事件才算平息下來。
土地承包到戶後,家裏的日子好過起來,分到家裏種的田地突然長足了勁,出產的糧食一家人吃不完。這時,母親就學習釀酒。酒釀出來之後,父親喝也喝不完,因為多,有時父親還用家裏的馬將酒馱到山街出售。高中畢業那年,我沒有考取大學,在家裏做農業,老家活兒苦累,牛糞要背到高山,那是糧食的糧食,水要從很遠的地方擔來,一天的生計才能維持下去。而所有解乏的辦法只有酒。於是喝起了母親的老白乾,父親也不再責罵我喝了他的酒,畢竟我已成人,老家有一種習俗,就是不會喝酒的男人是很難娶到媳婦的,只是後來酒量一天比一天大,不時還會鬧些醉酒的小事故來,父親才對我喝酒有所限制。
後來,來到城裏,先是在工地裏幹活,與許多出賣汗水的農民工呆在一起,喝酒是免不了的,喝的還是那種從鄉下捎來的白酒。鄉下人老實,不會在酒裏摻上甚麼有害物質,喝起來不傷心不傷肝不打頭。但老家離城很遠,不可能每個月都有機會喝到,老闆便到批發市場弄來些白酒,算福利發給大家,見老闆如此開恩,就都感恩涕零地喝了個大醉,不料那次所喝的老白乾係無證照勾兌的,裏面除了香精,糖精,酒精就是自來水,喝了之後許多農民工都出現了頭痛眼睛腫痛現象,再後來竟出現了嘔吐等中毒情況。不好,是假酒中毒。如果不是搶救及時,後果不堪設想。
進入機關單位,喝酒的機會多起來,逢聚必酒,逢酒必醉,逢醉必亂。酒的真味被這一個亂字搗壞,再好的酒喝起來只一個字可總結,那就是苦。不管是號稱國酒的茅臺還是價格不菲的五糧液,喝得一醉方休的時候,根本喝不出那杯是好哪杯是壞,哪杯裏有鄉下父母種出的糧食,哪杯裏藏着犯罪分子害人的東西。
算起來,喝酒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倒是與酒有關的愛好還值得紀念,一是收藏酒瓶,二是寫酒文章。收藏酒瓶,主要是收藏那些顏色獨特,造型漂亮,瓶上有書法,繪畫,詩詞等藝術作品的東西。不少字畫還出自名家,同時酒瓶上還記載着酒的歷史,典故,產地,性質等諸多信息,酒瓶不單是盛酒的工具,也是有豐富內涵的酒文化載體。寫酒文章,就是把聽到的酒故事整理出來投向報刊,當然最後是換一些買酒的稿費,不想寫着寫着竟加入了省作協,竟成了酒文化研究的一名會員,所謂的以酒養酒,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