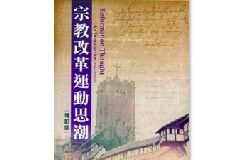藝文選讀
夏丏尊二論創作過程:
果戈里的“外套”

果戈里 Gogol
有一種創作過程,是由於作者聽到了或經驗了一件真實的事件,作者便利用了這事件而寫成他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卻已經換了面目,和那件原來的事實完全不同了。那一件真實的事件只是一點酵母,而作者的思想,經驗,就是那等待發酵的麵塊。那些麵塊本有發酵的可能,但非等加入那一點酵母不可。果戈里(Gogol, Nikolai Vasilevich, 1809-1852)的外套(The Cloak, 1842),便是這樣寫成的。在萬壘賽耶夫(V. Veresaev)的果戈里是怎樣寫作的(孟十還譯)一書中,作者說,外套的故事是由於果戈里聽了P.V.安寧可夫所講的一件真事而寫成的。那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次在果戈里面前講到一段公務員的逸話,是說一個貧窮的小官吏,他喜歡打鳥,又特別儉省,而且不疲倦地,盡心竭力地做着職務上的工作,終於積足了夠買一枝價值二百盧布的很好的獵槍的錢。在第一次,當他乘着自己的小船遊到芬斯基河灣去尋找目的物的時候,他把獵槍放在自己面前,照他個人的說法,他忽然墜入一種夢境裏去了,等他清醒過來,朝面前一看,不見自己的新買的東西了。那枝槍是在他通過的地方,被深厚的蘆葦掛掉到水裏了,於是他用盡全力地搜尋它,但是枉然。小官吏回到家裏就一頭倒在床上,再也起不來了。他得了寒熱病。他的朋友們知道了這椿事,便來發起募捐,給他買了一枝新槍,這纔救回了他的命。但這椿可怕的事件,無論甚麼時候他一想起來,就不免在臉上現出死人一般的灰白。…所有的人都笑這個具有真實的來歷的逸話,果戈里卻例外,他沈思地聽着它,低了頭。這個逸話便成了他的小說“外套”底初步的思想,並且這篇小說在那一天的晚間就在他的心裏生根了。

The Cloak by Gogol
事實是如此,但到了果戈里的筆下便完全不同了,果戈里完全把它重新創造過。像書名所表示的,代替了事件中的鳥槍,卻變成了“外套”。由於這一個改變,故事的一切也就不同了。作者為甚麼不寫“鳥槍”而寫“外套”呢?關於這問題的回答,大概只有向作品的主題和作者的生活體驗中去追尋。而且當他一聽到安寧可夫講那事件時,他就有一種特殊的認識在心裏,他不同別人,他有另一種感觸,不是好笑的,而是悲憫的;他也就有另一種思想,不是個人的問題,像只是一個人愛好打獵之類,而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像“外套”的主人翁所遭遇的,像故事的最後所顯示的。也正因為這些感觸與思想,一言以蔽之,因為了這一新內容,就非改成“外套”不可,因為,如果仍是“鳥槍”,那就無法,或不容易達到這個目的了。
“外套”的主人翁─當然不再是那個喜歡鳥槍的人─當安寧可夫告訴那件事時,不見得就描寫了那人的面貌,即使描寫了,也不見得就是果戈里筆下的人物,為了適合人物的性格,為了適合於這人物所演的悲劇,果戈里筆下的人物是:
身體矮小,臉有些麻,頭髮微紅,兩眼看來甚至有些眯睎,額頭上光了一小塊,兩頰有皺紋,臉上有那種令人呼為痔瘢的顏色…有甚麼辦法呢─彼得堡氣候的過錯。
就在這簡單的描寫中,我們也可以預感到我們這位主人翁的命運了。關於他的名字,作者寫道:
他姓巴甚瑪金,這個姓顯然是來自“巴甚瑪克”(意即輕皮鞋);但是在甚麼時候,是哪一點鐘,怎樣來自“巴甚瑪克”,這一層是一點也不清楚。父親,祖父,甚至內兄弟,以及所有姓巴甚瑪金的全穿長皮靴,一年不過換兩三次前掌。他的名字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
意即輕皮鞋的姓氏,這就彷彿注定了一些事物,但這是無可如何的,至於名字,那卻是經過了他的母親,教父,教母再三選擇的結果。當這樣的名字定下來了,作者說:
他們給孩子施洗,他因此哭了,並且做出這樣的苦臉,好像已經預感到他將是九品官似的。
他當然是作了九品官,他在一個司裏作了書記官,而且永無升遷,永無變化。
作者接着說:
於是,大家便確信了,顯然他生就是預備穿制服,光着頂的。司裏對他不曾表示任何敬意。看大門的不僅是不從位子上立起來,當他出入的時候,並連瞧他一眼也不瞧,好像從會客廳飛過一個尋常的蒼蠅似的。…
年青的官吏們,盡其公事房的小聰明嘲笑奚落他,當他面就述說各種編造關於他的故事;關於他的女房東,七十歲的老奶奶,說她打他,大家問他們甚麼時候結婚,向他頭上亂撒些碎紙,說這是雪。…不過要是鬧出太受不了的玩藝,當打亂他的工作,掣他的肘的時候,他開口說道:“莫動我,你為甚麼欺侮我?”並且在他發出言語的腔調裏,好像有甚麼奇異的東西似的。
作者說,在這樣的言語中,是有一種動人憐憫的意味的,在這刺人肺腑的話裏似乎響動着一種最謙卑的哀告:“我是你的兄弟。”他是一切人的兄弟,他願在任何人面前低首,即使稍稍反抗,也還是自卑的,屈辱的。
像這樣的一個人,在他的生活中還有甚麼可說的呢?他終日埋首抄寫,他在抄寫中有無限快樂,像其他人在他輝煌的事業裏有快樂一樣。每當他抄寫的時候,“享樂的神情現在他的臉上;有幾個字母是他心愛的,倘如遇到這些字,那他簡直樂得忘形:又是笑,又是眨眼,又是動起嘴唇,因此似乎在他的臉上可以讀出他的筆下所運行的每個字母。”可憐的人!在他的卑微的生存中,也還開着一些花朵,一些希望,無奈這卻只是幾個心愛的字母!而他也就安於這些,當他的上司看他熱心服務,命令他改變一下工作,不再抄寫,而作作“等因奉此”之類的工作時,他卻流着汗,拭着額頭,終於說道:“不行,不如給我抄寫一些甚麼倒強些。”他就一直這樣作下去,而且,不但在辦公時間切實服務,回家之後,還“抄寫帶到家裏的公文。倘使沒有這些事,那他為着自己的快活,便故意替自己抄個底,尤其是倘如這公文不是為着風格華麗而出色,卻是為着致甚麼新的或闊的人物的姓名住址。”他以全生命工作,他的生命和工作簡直融而為一。“他寫夠了便睡覺,想到第二日,明天上帝派他寫甚麼東西,就微微含笑。”這樣的好人,這樣盡忠職守,這樣不存任何奢望的人物,然而,他卻沒有方法不受彼得堡的寒冷的侵襲,“當連辦上等差使的人前額都凍得發痛,珠淚滿眶的時節,可憐的九品官們還毫無防禦呢。”
這以下,故事就開始了,他先是請求裁縫給他修理破“外套”,然而那已是太破了,破得不可救藥了,當他聽說必須縫製新外套的時候,他兩眼發黑,而且屋中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顛倒錯亂了,因為他沒有八十盧布─這是他估計的最低價錢,實際上裁縫討價是一百五十盧布。在這裏,為了進一步地發掘人性,作者寫道:
但是,究竟從哪裏拿這八十盧布呢?一半也許還可以得到!一半找得到,或者甚至再多一點,但是在哪裏找到別的半數呢?…但是讀者要先知道第一個半數他是從哪裏拿來的。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有兩種習慣,每花一盧布,便放一個格羅斯(合兩個戈貝克,即兩分),在蓋上帶有投錢孔的,被鎖住的小箱子裏。經過每半年他要查算聚集下的總數,將它換成小銀幣。他好久就這樣做,以此,繼續幾年,聚下的總數,有四十多盧布。那麼,一半已經是在手頭;但是從哪裏拿另一半呢?從哪裏拿另外四十盧布呢?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想了又想,決定要得減少平常的花費,雖說最低限度得繼續一年:每晚不用茶,每晚不點蠟燭,假如有甚麼要做,往主婦屋子裏,在她的燭光之下做活;走到街上,腳步盡力放輕,而且小心地踏在磚石上,差不多用腳尖子在走,為的不致很快地就穿壞了靴前掌;汗衫能夠對付就不交給洗衣服的人洗,至於想不致穿破,他每一次剛一到家,就把它脫下,光穿一件斜紋布的長衫,這長衫已經細心地保存好久了。老實說,他起初對於這些限制是有些難於習慣,但是以後已經弄慣,就很合適,─他甚至每晚學會了挨餓;不過在意思之中,卻含着將來的外套的永久觀念,作精神的營養。從這時起連他個人的生存也好像豐滿些,他好像結了婚,好像另有個人和他在一起,好像他不是一個人,倒像有一位生活上的快樂伴侶願意和他同走着生活的道路,─這位伴侶不是別人,正是那填着厚棉絮,有穿不破的結實裏子的外套。他彷彿變得活躍些,連性子也堅定些,有如那自己已經確定了目標的人似的。從他的面孔以及行為上自然而然地消滅了遲疑不決,一句話─所有搖撼不定的痕跡。在他的兩眼裏時常出現火光,腦海中甚至閃動着極果敢和奮勇的思想,莫非真是貂鼠皮放在領子上?這思想幾乎使他心不在焉。有一次,當抄寫公文的時候,他幾乎快要弄出了錯,所以幾乎高聲叫出“哦!”手畫十字。
啊,上帝!這真是人生中最好的時候了,年青人在向一個美麗的少女求愛,操必勝之心的將軍正要赴敵,一個偉大的建築正要立起,一個大帝國正要完成,一朵花正要開放,整個世界擺在一個人的面前,而我們的好人,一件外套就要完成了,這生活中最高的理想,最大的歡悅,而事有湊巧,司長給他的賞錢不是四十,也不是四十五,倒是六十盧布,多出來二十盧布,“這一來事情進行快了,再略為餓上兩三個月”,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一生中“最莊嚴的一日”終於到了。他穿上新外套,他心裏暢快極了。作者寫道:
他每一瞬間都覺得在他的肩上有新外套,並且甚至為心裏的滿足笑了幾次。實在不錯,有兩種利益:一種是暖和,另一種是美好。
偉大的作家,奇異的作家,他寫出了這麼平凡的句子,平凡得這麼出奇,這麼可怕呀,曾有那因久於飢渴而忘記了飯是可以充飢的,水是可以解渴的人嗎?這樣的人他將體會出這話的意義!到此為止,在人性的顯示上,果戈里的工程已經完成了。這以下,就是故事的突轉,春天正在繁盛,花開得正好,秋天來了,冬天來了,陰暗來了,寒冷與死亡來了。從個人的,到社會的,從生活的,到政治的,從“現在”的,到“將來”的,於是作者把畫面展開了。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穿了新外套到司裏去,人們的嘲弄,祝賀,使他難於為情,當大家一齊圍上他,說要喝新外套的喜酒,並且至少他應該給大家招個晚會的時候,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完全糊塗了,他滿臉通紅,說道:“這完全不是新外套,這只是一件舊的。”“終之,有一位副書記長,似乎想表示他為人一點不傲慢,而且和下等官員要好,說道:那麼,就這樣吧,我來替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招個晚會,今天我請大家到那邊喝盅茶:今天適逢是我的命名日。”到了晚上,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自然是參加了的,他剛到的時候,大家還圍着他的外套研究了一陣,但以後,“不消說,大家連他,連外套都拋下了,仍舊轉向指定玩啞牌戲的桌子。”他覺得無聊,便偷偷溜開,“他輕輕地從屋裏溜出來,在外間找到了外套,看見很可惜的躺在地上,將它抖一抖,從上面摘下了每個小灰毛,套在身上,順着樓梯走到街上去了。”外套被丟在地下,這也許就是即將到來的不幸之預兆吧,他回家的路是遙遠的,而且夜已深深,當他走過一個荒涼的廣場時,他就遇着了那些滿臉生着鬍鬚的人們,─“究竟是哪種人,連他也分辨不清楚。他竟兩眼發黑,心頭亂跳起來。‘這豈不是我的外套!’他們之間有一個抓住了他的領子,大聲說道。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已經想喊‘守衛’,恰好另一個人正對着他的嘴伸出一隻拳頭,大得有如官吏的腦袋一般,說了:‘只要你一喊!’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僅只覺得他們從他身上剝下外套,給他一膝蓋,於是他跌在雪上,仰着,別的再也不覺得了。”
他回家之後第二天清晨,為了要找回他的外套,他去見一位署長。這時,當時俄國的官僚們便搬上了舞臺。清早,他就到署長那裏去,但是說署長在睡覺;他趕十點鐘來,─又說:“在睡覺”,他趕十一點鐘來,─說:“署長不在家”;他趕吃午飯的時候─但是在前廳裏的書記不准他進去。終於見到署長了,署長“不注意事的要點,卻問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他為甚麼回來得這麼晚?他順便到不正當的人家去了沒有?”他的請求反而換來了責備。他這一天,生平第一次未到司裏去,第二天去辦公,他的不幸卻又換來了嘲笑,雖然有些人同情他,甚至想給他募捐,“但是集的太少了,因為沒有這事,官吏們訂司長相片和一本甚麼書,依科長的提議,他是著者的朋友,已經花費了許多;這樣,所以集款的總數極不中用。”以後,他又去見一位“闊老”。這位闊老,也許可以作為一般官僚的代表,他一切照極嚴厲的規矩行事:十四品官要報告十二品官,十二品官要報告九品官,或其他合適的人,這樣事情纔到了他的面前。…闊老的派調習慣沈着森嚴…他的法制的重要基本是嚴。“嚴,嚴,而且─嚴,”他同屬員的通常談話聲色嚴厲,多半是這一句:“你怎麼敢?你可知道你同誰說話?明白不明白誰站在你面前?”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去請求這位闊老的結果是顯然的,起初是擋了駕,等了很久,見到了,闊老罵他不懂辦事的規矩,罵他“你們青年人對長官真是放肆得太過分了!”殊不知他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他在歸途中迷了路,他“大張了一下嘴,在偏街嗚嗚響的暴風雪中向前走;風,照彼得堡的老例,從四面八方,從所有的小巷裏向他吹來。轉眼之間給他的嗓子吹起喉嚨病,臨他摸到家的時候,連一句話也不能說了。喉嚨全腫起來了,躺在床上。一頓好責罵有時是這樣厲害!”第二天他發了大熱。當醫生看過之後,轉臉向房東主婦說:“你好,媽媽,你不要白費了工夫,現在就給他定一口松木棺材,因為橡樹的於他是太貴了。”這期間,病人還要在不住的說着昏話。“一會他看見了裁縫,向他定做帶捉賊陷阱的外套,因為他覺得賊們不斷地在他床下;並且他甚至時時叫主婦從他的被窩裏拖賊;一會他問,他有新的外套,為甚麼在他的面前掛起舊的外套來;一會他覺得他立在一個將軍面前,聽着一陣好責罵,於是哀告道:有罪,大人!終之,竟烏七八糟臭罵起來,說出極可怕的話,這樣,所以連老主婦也畫起十字,她有生以來沒有聽他說過那類的話,尤其這些話是跟在‘大人’兩字的後面。…”“終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斷了氣。他房間裏的東西都沒有封起來,因為第一是沒有繼承人,第二呢,遺下的繼承物很少,就是:一把鵝毛管,一帖公家的素紙,三雙襪子,從袴子上落下的兩三個鈕扣,和讀者已經曉得的破外套。…”“司裏知道了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死,第二天在他的位子上已經坐着一位新的官吏,體幹要高得多,寫的筆道已經不用那樣直筆道,卻要斜曲得多了。”
寫到這裏,“外套”的故事已經完了,然而果戈里的創造還沒有完,果戈里還繼續寫下去,寫得更遠,更深,更荒唐也更真實,而且把歷史的預言也寫在這裏了。果戈里是最善於利用傳說,迷信,時聞等等,與最深的人性,與社會的政治的大問題攪在一起的,像鼻子(魯迅譯),像魏(孟十還譯),像初期寫烏克蘭的作品:是滑稽的,然而也是最莊嚴的;是可笑的,然而也是極可怕的;是沒有道理的,然而又是多麼的令人深思啊!他接着寫道:
但是有誰能想像這裏不真個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結場,他卻命定的在死後要哄動幾天,好像報答他從來不為任何人所注意的一生?…謠言忽然傳遍了彼得堡全城,說靠加鄰金橋旁和鄰近較遠的地方,夜間死人出現,像找尋被搶去的外套的官吏,並且藉口是被搶去的外套,他不分職業和品級,從肩上剝去各人的外套,無論是:貓皮,海獺皮,棉花,樹狸皮,狐皮,熊皮,─一句話,人們為着護身而想到的各類毛皮。…警察已下令捉屍,不論死活,嚴重處罰,作別個榜樣,連這也幾乎辦成了。就是,某地段的崗警,在克留什金小巷裏,已經一把抓住了死人的領子,正在作惡的地方,圖謀着剝下一位卸職的樂師身上的呢外套。一把抓住了死人的領子,他便叫來另外兩個同事,託他們抓着他,他自己費不過一刻鐘工夫往長靴裏去摸,想從那裏掏出樺皮鼻煙盒,略為清醒清醒自己凍得不得了的鼻子;但鼻煙實在是這一類的,連死人也受不了。崗警用手指閉住自己的右鼻孔,還沒有來得及把半掌鼻煙送入左鼻孔,死人一噴嚏打得這麼凶,噴得他們所有三個人滿眼都是。當他們拿起拳來拭眼的時候,死人的蹤影都不見了,所以連他們都不知道,以前他是不是真正在他們手裏。從此以後,崗警們對於死人恐怖到這樣,甚至連活的也怕捉,僅僅從老遠喊起:“喂,您,走你的路吧!”死官吏居然在加鄰金橋那面出現,引起一般膽怯的人非同小可的畏懼。
寫到這裏,應該是結束了吧,然而還不,作者還要把另一個線索拾起來,“但是,我們完全把某一位闊老拋下了,”於是他寫那位闊老,他,自從責罵了阿加克.阿加克維奇,這個小官吏的影子差不多每天現到他心上來,等聽說這個可憐蟲已經暴死了的時候,他甚至“傾聽着良心的譴責,而且整天心神不安。”關於這,我們必須相信,闊老的良心實在只是作者的希望罷了,作者要懲罰這些闊老們,所以這樣說了,而且還使那闊老也遭了厄運。他從一個晚會出來,要到他的德國女姘頭那裏去,─我們當不會忘記,署長曾責問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你為甚麼回來得這麼晚?你是不是到甚麼不正經的人家去過?”─在風雪中,死人出現了,向他噓出可怕的墳墓的氣息,說道:“哈,這竟是你呀!到底我把你的領子抓住了!我也要用你的外套。我的你不操心,並且還責罵我─現在把你自己的交給我吧!”他嚇得趕快就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向車夫喊道:“快快跑回家!”說也奇怪,從此以後,死官吏便完全中止出現了:
顯見得將軍的外套很適合他的肩胛,至少已經在任何處也聽不見有這樣的事情,誰從誰身上剝下外套了。不過有許多耽心好事之徒,怎樣也不想安靖,說在僻遠的城區死官吏依然出現。並且真是的,有一位珂羅綿地方的崗警親眼看見鬼魂從一家住戶後面怎樣出現;但是因為自己體質不強…所以沒敢使他停下,僅在黑暗裏追隨着,直到終之鬼魂猛然回頭一望,停下問道:“你想要甚麼?”而且顯出這樣的拳頭,在活人身上也找不着的。崗警說道:“沒有甚麼,”並且立時轉回去了。可是鬼魂的體量高得多了,留着很大的鬍子,並且,他的腳步,顯然是向阿布禾夫橋上走去,完全隱沒在夜的黑暗中了。
小說就這樣作了結束。這結束使我們作何感想呢?首先,有幾個特殊的印象將永久留在我們的記憶中:當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被劫的時候,作者說那強盜的拳頭之大,有如官吏的腦袋一般。大老爺們吃得腦滿腸肥,腦袋自然是很大的,然而作者的意思毋寧是說:那肥大的腦袋卻是當作了巨大拳頭,這拳頭是專向窮人們的臉上打來,這一打是專為了劫奪可憐的同類的。當那位闊老自己也造出了鬼怪,自己把外套扔丟之後,作者寫道:“從此以後,死官吏完全中止出現了:顯見得將軍的外套很適合他的肩胛…”是的,又有甚麼不合適的呢?受壓迫者的寒冷正是為了壓迫者的溫暖,讓溫暖得太久的應當嘗一嘗寒冷,讓寒冷得太久的應當也得到溫暖,這個世界實在應該倒置一下,改造一下。所以作者最後說,警察的力量太小,而且也太膽怯,因為到處有鬼,而且,鬼魂的體量高得多了…。鬼的增高與長大是象徵着甚麼呢?說得遠一些,說果戈里也作了那大改造的預言也許並不怎麼過分吧。從這樣看,如說果戈里是不懂得俄羅斯的生活,說他沒有思想,─像某些批評家所說的─當然那是不見得全對的。至於這是不是一個鬼怪故事,─像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麗姬亞(Ligeia)那樣─當然也不成問題。作者說:“警察已下令捉屍,不論死活,嚴重處罰,”這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可能,正當其時,社會上也許正傳說這樣一個鬼的故事,這裏的荒唐可笑是多麼令人相信,令人可怕,而“麗姬亞”的借屍還魂,雖然愛倫.坡在嚇我們,我們不怕,雖然他在逼我們相信,我們卻不相信他。在這裏,兩種作品,兩種創作過程,孰優孰劣,可以明明白白了。
但是,最後,我們也許還記得那“鳥槍”的事實。然而那有甚麼關係呢?沒有關係,那只是一粒種子,一個火星而已,假如作者寫的小說是“鳥槍”,而不是“外套”,我們將看見甚麼呢?那末,作者是憑了甚麼本領而創造的呢?難道他真遇到過這樣的事嗎?沒有的,像萬壘賽耶夫所說的,他是憑了一種“推測別人的能力”而創造的。他自己也承認他有這樣的本領,他說:“我是一個鑑賞家,如果靈魂有一點兒露到外面來,它就逃不開我了,當沒有開口說話的時候,我便先在臉上看見它了。”他又說:“上帝把聽取靈魂的美麗的感覺放在我的靈魂裏了。”他在一封寫給柏林斯基的但沒有發表的信裏也說到存在於他身上的這種“慧眼的天才”。這誠然是一種天才。但甚麼是天才呢?像我們曾經講過的,天才者,就是那靈感最富的人,就是那想像力最高的人,而所謂創作是經驗的集中而終之造成一個全新的世界,而經驗之集中是憑了想像力的。我們可以說,“外套”所表現的這一切都是新的,因為它是作者的創造,但也可以說都是舊的,因為它必是早已含在作者的生活裏,藏在作者的生命裏,這些東西,像一些可燃的東西,但必須等那一點火星─“鳥槍”的事實─來點燃它,一經點燃了,於是就灼了起來,而且灼起來成為一團火。我們可以相信,當果戈里聽安寧可夫說那“鳥槍”的事件時,他的生命一定受了震盪,就在那一頃刻,他就受了孕,由於他對於人生世事之體察人微,瞭解深切,由於他的文學修養,他的想像力之強,可能在那談話的當時就已經有一個“完整的世界”在“煥然地覺醒”了,那就是所謂靈感之一閃。但也不一定,也許他懷孕較久,他當時也許並未完成那個“完整的世界”,他再思索,再體察,也許不知又隔了多少時候,他終於懷胎十月而生產了。這樣的創造過程是絕不同於愛倫.坡的“麗姬亞”之創造過程的。他不從觀念出發,卻從事實出發,任可事實之中都有“人性”,都有“意義”,都有“道理”,然而作者並不用這事實,甚至不用這人物,這意義,這道理;他生發開去,拓展開去,加深下去,由於他的生活,思想,情感,總之,由於他自己的看法,他創造了新的東西。![]()
(選自夏丏尊:作品漫談)
翼展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