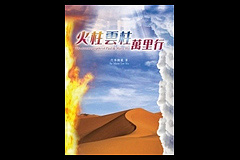從聖樂看作曲家最後的心靈超越
從音樂家生命末期的作品,看到他如何反省一生,而尋求上帝救贖的手。他們也許不是偉大的音樂家,也許不是偉大的音樂作品,卻是真誠的救贖渴求而讓人感動不已。
我能收集到的最早期的聖樂,就是葛利果聖歌(Gregorian Chant)。那是一種非常重禮儀和歌詞的聖樂,曲調單純在幾個音符間滑行,沒有和聲,沒有分部,也沒有女聲。我常聽人家笑葛利果聖歌簡直就是在唸經。
近年暑假我去了一趟歐洲。就在維也納,我被蓋於約西元1100年左右的聖司提反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震撼了!

聖司提反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
初見教堂的外觀,我就覺得這古老教堂會說話。
教堂因年代久遠,外表露出像被煙燻過的黑色色澤,而教堂裏面,充斥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我發現所有的遊客,不管在外面是多麼的喧嘩,進入這教堂,都跟我一樣立刻安靜下來。

教堂裏面透着沁涼。堂頂高遠。地下室,放着數座老死於此教堂的主教神父們的棺木,也是年代好久遠了。
我安靜坐在椅子上默想,想這教堂歷經戰爭浩劫,竟奇蹟似的存到如今,見證人類生命的短暫,在浩瀚歷史中實渺滄海之一粟,唯有教堂高聳指向的上帝榮耀,是從亙古直到永久。
現在流行一種文化復古風潮。非洲的,南美的,中國中原的,以及葛利果,都在這風潮中突然走紅起來。當我坐在音響前面聽葛利果時,腦中浮現那會傳講歷史的古老教堂,以及中古時代的質樸人們,坐在教堂裏跟他們屬靈的父親吟唱對答,心中不禁露出一個疑問:現代人對葛利果的熱愛,有多少是出於對宗教信仰質樸的需要?

阿雷格里 Gregorio Allegri
葛利果聖歌之後開始出現對位曲式,那時到了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樂還沒有明顯的貴族氣息,仍舊十分清純,對位,又給聖樂帶出許許多多的變化。我最喜歡的是阿雷格里(Gregorio Allegri, 1582-1652)的“垂憐曲”(Miserere)。據說這首曲子被教會緊緊收藏了不外流,怕被一般俗人破壞了其樂曲的神聖性。垂憐曲歌詞取自詩篇第五十一篇,曲式中緊連三段節節升高的樂段,將詩人大衛出自內心深處的懊悔表露無遺:“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據說,是神童莫札特(W. A. Mozart, 1756-1791)去教堂禮拜,聽到這首曲子後,心中立刻記牢了,回家默誦出來,終於讓曲子流傳出去。有時候,當我心中有些重擔,是無法用言語禱詞說出來的,我就在這首曲子面前沈默,讓音樂表達出我心靈深處的祈求。
音樂史上的巴洛克(Baroque)與古典(Classical)前中期時代,算是聖樂的高峰。重要曲目如巴哈(J.S. Bach, 1685-1750)的“馬太受難曲”(St. Matthew Passion),韓德爾(G. F. Handel, 1685-1789)的“彌賽亞”(Messiah),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的“創造”(The Creation),都是這時代的產品。但就其聖樂產量之豐,與好作品的比例而言,這兩個時代卻出現過多的拙劣之作。韓德爾有太多作品沾染意欲討好貴族的企圖,華麗喧鬧但不清純,很難釐清是為獻給上帝還是獻給貴族。莫札特在薩爾斯堡(Salzburg)期間,自己都承認:“做宗教曲目是應要求而做,至於我自己呢!還是離敬虔越遠越好。”那時他很年輕。到將離世前幾年,因為生活過度不節制,創作量太大,感染肝腎病變,其作品才突然躍升,像得到某種神秘啟示似的,出現極品。海頓呢!實在太拘泥於格式,好像真正的禮拜敬虔,都被某種形式框住,無法自由的向上帝傾訴。海頓晚年覺得他這一生的音樂創作,一直少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後來悟通,寫出“創造”(The Creation)這頌讚上帝創造的聖樂曠世巨著。“創造”的頌讚,才真的讓人覺得不再受某種格式囿限的,打破框框自由與上帝交談。
 巴哈 J.S. Bach |
 韓德爾 G. F. Handel |
 海頓 Joseph Haydn |
 莫札特 W. A. Mozart |

孟德爾頌 Felix Mendelssohn
或許那樣的時代,正是中產階級與貴族勃興的時代,在他們的優裕生活與某種跟宗教領袖奪權過程中,宗教變成一種約定俗成的想當然已,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優越典雅的文化,因而扼殺了心靈誠實的向上帝禮拜,也無意鼓勵作曲家的敬虔。形式,就變成一種溝通方式,一種彼此保護。巴哈是個例外。他卻窮困潦倒以終。最偉大的“馬太受難曲”,竟然是百年後讓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來發揚光大。而“馬太受難曲”,對基督受難的過程,是用了多少的情感來詮釋的啊!
當我聆聽這時代的作品,有時竟會出現一種戰慄感。因為我在我們這時代,一樣看得到某種華而不實的信仰,以及可以將華而不實包裝起來的形式。
浪漫時代(Romantic)已是個經過宗教改革的時代。不管是蛻生而出的基督教,或透過耶穌會刺激出來的天主教,都開始着重個人與上帝之間獨特的關係。浪漫時代的作曲家,地位也較能獨立,既不受制於貴族,也不受制於教會。浪漫派因此像一個有非常多選擇的十字路口,在掙脫束縛後的激昂人性裏,自由的選擇是向上帝或背離上帝。
銜接古典與浪漫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已經在其“莊嚴彌撒”中,透露出不為形式拘格,出自心靈深處很人性的向上帝的吶喊,尾隨而至的浪漫時代,更在音樂家創作的曲子中,處處顯露神性的與人性的交戰。
譬如古諾(Charles Gounod, 1818-1893),終生想作神父,卻終生作了作曲家。其宗教音樂就充滿了激昂的向上帝的熱情。
 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
 古諾 Charles Gounod |
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終生自由選擇的向上帝虔誠,卻一直無法斷掉其風流韻事,直到晚年,終於不顧一切的進修道院做修士,期望其內在神性終能戰勝人性。
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 1792-1868),早在青年時期就因戲劇大大出名被肯定,卻在聲望最高的三十七歲,突然完全停止創作,沈寂十多年。當他再復出,創作的竟是聖樂。他在音樂中放入他的禱詞。離世前幾年,羅西尼創作了一首他唯一的彌撒,在應當是最悲壯的垂憐曲中,卻仍舊是他一向的戲劇玩世不恭的風格。他為此很懊惱,向上帝禱告說:“或許我天生只能做戲劇家,但我好想創作聖樂獻給你,也希望你悅納。”
 李斯特 Franz Liszt |
 羅西尼 Gioachino Rossini |
浪漫時代是神性人性交戰的時代,在人透過宗教改革掙脫教會控制,獲得充分的宗教自由,人徘徊在十字路口,在上帝與自我間掙扎做取捨選擇。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有可能是最壞的時代。
然後就發展到二十世紀。時代背景告訴我們商業物質侵蝕着世人向靈性發展的渴望,民主的相對性拆解掉相信有絕對真理的可能。現代到後現代的藝術文學發展,甚至拆解掉人自身的主體性。一切都可被懷疑,一切都可被拆解。這是無信仰的時代。而現代聖樂,就透過無調性,不諧和音,呈現“存在主義”式的吶喊上帝。與其說是頌讚上帝,毋寧說是吶喊出人跟上帝的疏離。這是聖樂的底線。越過這條底線,就是“新時代音樂”,上帝消失,只剩下泛靈。
現代聖樂給人的感覺是焦慮的。但仍有幾支清流。一是黑人靈歌(Soul music)。黑人靈歌雖帶出藍調(Blues)爵士(Jazz),以及現在我們習慣接受的“敬拜讚美”式聖樂,但早期的黑人靈歌,卻是黑人苦難中向上帝的盼望。最著名的幾首黑人靈歌,都陳述出苦難,以及信仰的堅定不移。另外,就是猶太人的詩歌,以及俄國詩歌,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長期活在苦難中的民族。
原來聖樂一樣是譜出一個聖經約伯式的真理:人類透過苦難,便將信仰濾掉了不純的雜質,顯出誠摯的信心,盼望,與向上帝的愛。
浪漫時代掙脫巴洛克與古典時代的教會權威框框,卻在神性人性交戰後,自由選擇了走進拆解真理無神無信仰的焦慮框框裏。然後在二十世紀末,突然出現了對最古老聖樂葛利果的發燒熱,並配襯着一股宗教復興的文化背景,包括基督教的,更多是各種靈異的。誰知道在科技一日千里之刻,人類心靈卻往返循環週而復始的在繞圈圈,這告訴了我們甚麼呢?如果聖司提反教堂有生命,應會傲然微笑,應它早在九百年前,就得知人類用歷史文明苦苦追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