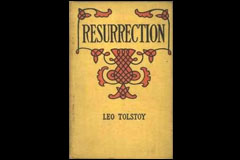貝多芬音樂中“自然”的過渡地位

一般人對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音樂最直接的感受,很少會用上“愉悅”兩個字,乍聽之下都會感覺貝多芬前中後期音樂風格是有轉變的,彷彿他的音樂是在跟隨他的心靈哲思,他的心靈哲思企圖以音樂的抽象性陳述出來。
的確,貝多芬的音樂是沈思的,哲學的,有話要說的,他的音樂對主題的鋪陳與不斷強調也是很有特色的。因此,聽貝多芬的音樂,我們會感覺嚴肅,甚至有點沈重。
走進大自然的悲劇英雄
但是,貝多芬的第六號交響曲“田園”,卻出現了少見的類似舒伯特式的優美。
這首交響曲,後人大致有共識的標示出主標題與每樂章的小標題,完全與鄉間自然之景有關。曲子在一開始就呈現一片祥和熱鬧,生機盎然,樂器齊出的活潑,彷彿要讓人一眼就望盡所有的風景。而這首曲子,尤其是第一樂章,透過長笛與豎笛的合奏,也尤其別緻的製造出屬於大自然之聲的優美。
但是,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是緊接着命運交響曲創作出來的,命運交響曲的著名程度,幾乎成為貝多芬的正字標記。貝多芬在“命運”中,銜續着其“英雄”交響曲的哲思。兩首曲子有非常相近的曲風,包括勝利似的鼓聲,法國號,沈重的斷音音節,以及由雄壯走向悲壯走向睥睨似的勝利感,這就是為甚麼大家都把這時期的音樂詮釋成“悲劇英雄的奮鬥”。這時期的音樂是在處理“人”而非“自然”,人面對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對必然導致的悲劇結局,卻絕對不被打垮的決心,甚至是誇耀自己意志力的勝利。這是典型的悲劇英雄主題。
為甚麼突然由這主題走向處理大自然的田園風格呢?而且兩首曲子緊鄰着,幾乎是同時在思考人與不可抗命運的搏鬥,並人進入大自然的愉悅感。
人作為主體 VS 自然作為主體
正是兩種哲思的交織並行處理,我們可以揣想而得,就算田園交響曲是處理自然界,身為“主體”的人,是不可能像華人文化中的國樂一般,完全消融進自然天人合一的。人勢必會突顯於自然界之中。
所以田園交響曲會處理田園中農人的歡樂慶典(第三樂章),立即伴隨暴風雨(第四樂章),再伴隨暴風雨後的牧歌(第五樂章),三樂章一氣呵成,於是田園交響曲就不只是呈現自然界的愉悅,也把人—自然間因風雨無情而不得不產生的對立生動的刻畫出來。
這種在自然界中的人的主體性,在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中更是以一種極藝術的美感鋪陳。
第七交響曲音樂一開始,就暗藏着玄機。它不像第六交響曲,以明朗一洩全出,它的序樂一直隱伏着,按捺着,甚至有點緊張的,彷彿某個事件即將發生…,直到引導到高潮,主角出現,是長笛的飛舞,像個活潑的精靈一般跳出,既是自然界中之生物,卻又不按自然界之牌理。這個精靈在眾樂器的伴隨下,舞姿優美,動感十足。但這精靈顯然並不是沒有困擾。貝多芬用轉小調,用休止符,用漸緩的猶疑感,讓人感覺出這精靈的舞蹈背後是有困頓之處的。但這樂章仍舊以歡愉結束。
在第一樂章的襯托下,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的第二樂章,就加倍的悲涼了。因為第二樂章長笛獨奏仍隱伏於全曲中,給人跟第一樂章銜接的感覺,可是不再是精靈的舞蹈,卻彷彿是狂歡後的寂寞與悲涼,尤其是第二樂章後半段的賦格特別明顯。不過,貝多芬因着輔以穩健的節奏感的處理,製造出一種毅然決然的感覺,那悲涼就成為英雄式的了。
因此到這裏,我們會看出貝多芬第五,第六兩種主題交織下,於第七交響曲達至某種融合,既有田園,也有主體人文的鋪陳。透過這種交織,少掉那種奮鬥,不甘與悲劇英雄的勝利感,但多了些優美,歡愉與舞蹈,雖然這主體仍舊是有悲涼感受的,但貝多芬把這感受潛伏下來了,不再是樂句中最想強調的主題。
當然,潛伏下來,並不表示它就不存在了。我們將會從貝多芬後來的音樂中,再看到悲劇性的主體重回音樂的主軸。
“人”作為主體與“他者”作為主體的對質

當貝多芬把音樂主題焦點集中於大自然,的確是進入他心靈歷程的另一個階段,一種從對抗,控訴命運的心境,轉入逍遙於大自然的心境。只是貝多芬從來沒有把身為人的主體性忘懷過。
後來貝多芬有近十年沒有創作。就一個藝術家而言,停止創作,往往意味着心靈歷程的暫時停擺原地踏步。這是人之常情。沒有人可以不停的心靈成長的。但是,這也意味着蟄伏後的復出一定有重大的突破。
果真,當貝多芬再開始創作時,我們從他的莊嚴彌撒與第九交響曲,看到過去貝多芬關切的主題竟然又重新回來了。
譬如說“莊嚴彌撒”,貝多芬自承這首曲子不是為了宗教儀式而創作,純粹是為了想用彌撒曲式說出自己的話。正因為這樣,這首彌撒是不能被教會儀式使用的,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當成是一首表白心靈的純粹音樂。
我們若仔細研究“莊嚴彌撒”,會發現這首曲子的天人交戰,絕不亞於命運交響曲。竟然過去貝多芬關心的音樂主題,重返創作中了,甚至比當年要更激烈。因為“莊嚴彌撒”中有另一個明確的主體,就是一位“他者”—上帝。當第一曲“垂憐經”一出,我們立刻可以聽出那種吶喊,是抗議命運不公的主體,向容許命運不公的上帝吶喊的心靈交戰。
這種天人交戰,到第二曲“光榮經”更是明顯,那鋪陳上帝榮耀的華麗樂句,和祈求垂憐時的悲愴,真是天與地的差別。而貝多芬調和這天與地的距離,就是用歌頌上帝時突然聲量急遽轉弱的收音,彷彿是要提醒上帝,因為人仍在悲劇中,歌頌難免有點不甘!
甚至最平和的第四曲“聖哉經”,我們一樣可以聽出貝多芬對垂憐,祈求悲憫的強調,而第五曲“羔羊經”,那企望上帝賜平安的祈求吶喊,也是要透過一再反覆,才由沒把握的,走向肯定句的。
文化對比
這種天人交戰的聲樂,只有對命運不甘的主體,遇上另一個可以被質詢的主體時,才會出現。因此莊嚴彌撒樂句的呈現絕不像一般彌撒曲,只把焦點置於上帝。它更強調主體與主體的對質。
談到這裏,我們回顧一下國樂。國樂幾乎是沒有憤怒,吶喊的心境表白的。所有悲歡離合,在國樂中都是以“哀怨”之情緩緩洩出。那種樂音的傾洩,幾乎可說是獨白,就算有聽眾,也可以確知聽眾對傾訴者的悲情是無須負責,但也無能為力的。國樂絕不是抗命的申辯,憤怒的吶喊,國樂是認命後的情感壓抑,也因此哀怨之聲讓人有徹骨之涼。譬如“妝台秋思”,“陽關三疊”,“胡笳十八拍”皆是。
國樂會如此,當然是因為華人文化中“天人合一”觀照之上,不再有創造者,也就是一個具有情感與意志的“他者”,一個可以讓人對吼的主體。天地大自然固然可以讓人消融其中,但天地大自然也是沒有情感,沒有同理心的,也因此才有“天地不仁”的說法。
身陷卑劣命運,卻面對無愛的天地,當然要不學老莊逍遙,一如國樂中的“夕陽蕭鼓”,以君子期勉自己,一如國樂中的“月兒高”,或哀哀怨怨的無助傾訴,一如“長門怨”了!
書寫遺書?心靈歷程的躍升?
莊嚴彌撒之後,貝多芬便創作了第九交響曲,也就是知名的快樂頌交響曲。
第九交響曲,簡直就是貝多芬過去所有心靈歷程的大集合。這曲子第一樂章,一樣把命運感鋪陳出來,諸如法國號,鼓聲,並與命運感相關的簡短有力的節奏,甚至在第三,第五交響曲中都出現的英雄命運式的賦格,也重返了。而樂章最初,貝多芬的樂句彷彿是一場戲劇的序樂般起始,恰似告訴聽眾:我正把我這一生演出來…。
第九交響曲不止讓命運主題重返,包括悲劇英雄睥睨命運的勝利感,田園風格,也隨後在二三樂章出現,第三樂章田園風格中,還暗藏命運似的樂句主題,提醒人逍遙世界中,主體還是人而不是自然。人永不可能融入自然。
第四樂章,光是很長很長的序樂那充滿悲劇感的小調,貝多芬就把一二三樂章的主題都植入了,然後先以命運風格,快樂頌二主題交雜出現,最後以快樂頌結尾。然後出現大合唱。
從這種鋪陳第九交響曲的方式,我們不得不說,貝多芬是在對過去作一個總交代總整理。因為英雄,命運,悲劇英雄的對抗與睥睨命運,進入大自然,狂歡,全在這首交響樂曲中出現了。
整理交代過去,只有兩種原因。一是書寫遺書,一是預備要進入另一個心靈歷程。
“他者”作為主體 參與進“自我”作為主體的人生命運
果真沒多久,貝多芬譜出他最晚期的作品,著名的弦樂四重奏。
貝多芬最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很多人都說很難像過去的作品那般的分析,也比較難理解。因為這時期的作品貝多芬已逾出古典樂派的形式太多,變得自由不拘格,他過去一直處理的沈重的英雄對抗命運的風格,和歡愉的田園風格也不復現,調性轉換與變奏形式都更加的任意。
這種曲風,無寧說是自己跟自己的告白,是從外在世界進入寂靜的心靈世界。
但是,我們有理由說,這種告白過程,“他者”之做為主體,角色有很明顯的轉變。
譬如貝多芬在曲子標題上加上“病後恢復獻上感恩,用伊里安調式的讚美詩式曲風”(op.132),或甚至在曲子一起始,就用聖詠式的賦格(op.131)。這些跡象都顯露,貝多芬是進入另一種心靈境界,就是把過去吶喊的,祈求的,高高在上威嚴的上帝主體,邀請進入他的心靈,參與他的告白與冥想。這個主體不再是他抗議的對象,而是跟他一齊回顧生命歷程的同伴。
這是何等大的轉變呢!
“他者”進入自我生命後的大和解
最後的弦樂四重奏,貝多芬除了擅長使用不居形式的變奏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頻繁的使用雙主題賦格。
雙主題賦格一定會給人一種感覺,就是在同時處理兩個很關心的命題。過去貝多芬曾同時處理命運與田園,但終究有先後順序,且其中一個主題隨後淡去,另一個主題隨後凸顯,這是一種時間上必然的交錯。可是雙主題賦格就不一樣了,雙主題賦格是在同一時間中處理兩個命題,並無一主題淡去,另一主題越來越明朗清楚的時間交錯。
這不僅是高難度的作曲技巧,最重要的是,以貝多芬音樂中的哲思特點,這已清楚陳述貝多芬到生命最晚期,已去蕪存菁,只剩下兩個懸疑的命題要解決。
貝多芬生前最後一首曲子,也就是弦樂四重奏op135,貝多芬自己透露出這兩個命題的基調。一個主題是嚴肅的基調,貝多芬自己寫下:“Must it be?”,另一個主題是輕快的基調貝多芬自己寫下:“<It must be!>”這就是貝多芬臨終前要處理的雙主題,但是卻不再是抗議的,吶喊的,只剩下沈思,與接納後的平靜。貝多芬自己就在第三樂章寫下標題:“<Peace>”而第四樂章,貝多芬又從嚴肅的“Must it be?”與輕快的“It must be!”雙主題交錯進行下,以輕快幽默的撥弦結束整首曲子。
那個曾被他抗議着,求告着,吶喊着的主體,在邀請伴隨進入他的內省世界,一齊面對他的一生之後,終於讓貝多芬平靜的輕快的幽默的接納了他的一生。他終於和解了。跟自己和解,跟命運和解,跟上帝和解。
無法言說的神祕歷程
貝多芬這一生最匱乏的就是愛。他父親暴戾,他自己總是陰錯陽差的無法結婚,他很早就有嚴重的聽力障礙,必須輔以“腦海中的樂符”來創作,晚年又被他想認養晚年作伴的姪子背叛…他這一生一直沒有愛。因此他的音樂嚴肅深沈,甚至是嚴厲的,到了晚年的大和解,是多麼讓人不可思議的一個心靈歷程。這是一種神祕體驗,是貝多芬只能透過音樂來言說的神祕,而我們,也必須透過這種聆聽,進入那不可言說的,兩個主體間的從對抗吶喊,到哀告,到成為生命的陪伴者的神祕歷程。
貝多芬的臨終之語是:“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這正是和解之語。![]()
※請參“華人音樂中的人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