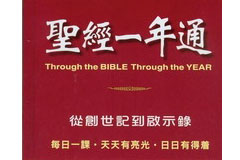韋列論翻譯
現代的華人,洋文學了多少,中文卻是丟掉了,甚至以為是羞恥。也許,再過些時候,華人到中國去,不懂中文,還需要請人作翻譯;不免請洋人作翻譯,那可有意思了,而且有人還能以為光榮呢!
過去的年代,洋人中的宣教士,真箇夠這樣的資格。現在因為華人競學洋文,宣教士學了中文,就無“用文之地”,所以差會索性不要求他們花那種時間了。
洋人對中文學得通,學得好的,我們都知道的,有蘇格蘭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香港牧會並作英華書院的校長三十年,把中國古典文學譯成英文。1873年回英國以後,作牛津大學的第一位中文教授。

韋列
晚近的英國東方語文學者中的韋列(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不僅是漢學家,也通日文及其他東方語文。他出版翻譯的一百七十首中文詩,多首日文詩集,並別的文學巨著。韋列曾任大英博物館助理書畫部主任,後任倫敦亞非研究院教席。以下是韋列談翻譯文學作品注意的事,雖然不是嚴格的專門性論著,只是散談,卻深有見地,可為有志文學者參考。作者要求較苛,說話也較苛,讀者該諒解。
我現在要說的,似乎淺顯,卻不是真箇淺顯,否則人就不會屢屢疏失,甚而故犯了。
翻譯的目的不同,體裁自亦有別。如果譯法律文件,只需作到達意該就可以了﹔如果譯文學作品,在顧及文理之外,還要求能抒情﹔因為在原作中,作者注入了他的情感﹕激憤,憐惜,歡悅。在作品中,涵有他的韻律,他的強調,他特意的選字遣詞。如果譯者在讀時體會不到,只是簡單的來上一串無節奏的字典意義,或以為是“忠於原作”,自詡“信”譯,實是誤傳。
在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或譯世尊歌)近結尾的地方,有一段極美而有力。武士有修(Arjuna)得到天神的指示,勝過了他一切的游移不決。因為那是在戰爭中,他必須要奮戰,雖然對敵是他的親屬或朋友。他的話,被譯成幾種不同的標準譯文﹕
一 啊,那永不差失的一位﹗靠你的恩典,我的無知被銷
滅,並且我已經得着記(屬於我的責任),我(現在)不
再疑惑,我現在將作奮戰,如你所告訴我的。
二 被銷滅了我的夢幻﹔靠爾恩典,毗濕奴(Achutya),
知識已被我得着。我立定不再疑惑﹔我將遵爾言而行。
三 我的迷亂已消逝遠去﹔我已得着記憶,靠爾恩典。
啊,從不錯失者﹗我站定不再疑惑。我要行爾言。
四 我的夢幻已被銷滅﹔我已得着記憶,靠爾恩惠﹔
啊,那堅定的一位,我被堅定,我疑已去﹔我要行爾言
譯例一的缺點,在無韻律之美,加上毫無理由的顛倒語詞次序,並且並不必要的加上括弧內的補文。任何讀者如果讀詩到此地步,還需要人告訴他詩中有修所記起的跟他立願去作的是甚麼,此君必然是粗心得出奇,也就不值得去俯就他。
譯例二比較好些﹔但Achutya這個稱號,對譯文讀者並不表達任何意義,似乎依其餘三位譯者的作法意譯較好。但是四位譯者都力求保持梵文語風,譯作“得以記憶”,以代替“記得”,是否有任何理由﹖
譯例三,如果在“消逝”之後沒有“遠去”二字,會使韻律好一些﹔贅加“遠去”並不會增加美感。但照我想來,譯例三(巴特耐教授譯)是四者中最好的。
譯例四給“我被建立”所破壞。雖然,在原文語源上是對的,但不可能是“我持此立場”的說法;其意思是:“我已決定”。
建議譯法大致如下﹕
你,不朽壞的神﹗
已破碎了我的幻夢,
靠你恩典我記起了,
我持定立場,我不復猶疑,
我願行你命令。
我不諱言,這只聊勝於原作的無力迴響﹔但我想,比以上的譯例略為有力而合韻律。無疑的,所有四個譯者,都懍於他們是在應付一首美妙的詩中最微妙的一刻,但我不認為他們的譯文能表達出這種情感。
在關鍵性的一段或行間,從開始譯者會實際感到那是極重要的,要把它譯得準確,不是搬移或粗略約意可以了事的。在源氏物語中的“浮舟”將近章末有這樣一段﹕浮舟在兩個情人中間無法決擇,定意自己投河。她女婢右近的好主意,反使他煩惱。
這一段照字直譯是這樣﹕
右近,近躺臥處,那樣作。“只有當人思想事物,因為那人的靈魂思想事物時迷失,實在易於有可怕的夢。當你決定如此或如彼就接近成功了。”這樣,她嘆口氣。[浮舟]展開軟布在她臉上,躺着,就是如此。
這裏所說的夢,顯然是指浮舟的母親在前一夜裏所得那“說起來怕人”的那夢(正如譯注者所指出的)。
我對這段的翻譯﹕
右近來陪她小坐。“人如果像你這樣,折磨自己,我們都知道會有甚麼結果﹕靈魂脫離軀殼,在那裏游蕩,因此給你母親得那些惡夢。沒有甚麼好疑慮的。自己打定主意或這或那,自會凡事大吉。至少是但願如此。”說着,嘆口氣。浮舟用柔軟的床單蒙着臉躺在那裏。
右近,當然不是一個土包子。但跟浮舟相比,是處於極低下的社會階層(雖然,即使在照字直譯時我也不曾想提出),這在使用動詞時表達出來。我們必須使她顯然用婢女的口氣同女主人講話﹔但要記得,她是浮舟的老乳母的女兒,是她的心腹女婢。我們必須表明她這種好心腸但無用的主意,絮聒得浮舟趨於無望。是不是我捉摸過甚破壞了這深刻的一段﹖我不以為如此。在約二十五年之後,我又再翻看過,仍然不想作任何修改,甚至感覺如果右近說的是英語,她大概也會如此說法。
沒有別的譯文可以拿來跟我的這段比對。如果有的話,或許會使我忽然感覺我譯的是一團糟。我所想到的是我譯過一段日本“能”劇卒塔婆小町﹕
啊,她從何等絢斕中失落﹗
怎地冬天的蒼白
冠戴了她的頭﹖
何處去了那可愛的髮綹,雙結
青絲螺髻﹖
稀疏的枯髮,如今失去了鬈曲
在枯槁的皮肉上,
那雙彎彎的蛾眉,消褪了
遠山黛色。
這是我在1921年所譯如此,不能算是劣詩。但是在最近我讀到布洛克譯的卒塔婆小町,刊於祁尼(Donald Keene)的文選中,我的信念有些動搖了。他對這段的譯文如下﹕
怎地那般的嬌艷失去了﹖
甚麼時候她變了﹖
她的頭髮一團經霜的草
覆頸的青螺在哪裏﹖
顏色消褪了從雙彎的峰巒
在她眉間。
我立即覺得,我的譯文是無可救藥的冗贅複言,並且不合試圖改進原文。我並不對布洛克(Brock)的譯作完全滿意;如果我的譯法太過於詩意,他的則失之於太散文化﹔無論如何也難以使我信服“在她眉間”之句堪為佳詠。
在中國小說西遊記裏,有很美妙的一段。唐三藏在涅槃之後,看到他褪卸的塵軀隨水流逝去﹕
三藏驚愕注視。悟空笑着說道﹕“師父,那是你﹗”豬八戒說﹕“是你,是你﹗”沙僧撫掌喊道﹕“是你,是你﹗”那渡者也應聲和道﹕“你去矣,可喜,可賀﹗”
海倫.赫斯(Helen Hayes)1930年的意譯本,這樣說﹕
一具屍體沖過他們旁邊。師父看了怕起來。但孫悟空在前面說﹕“師父,不要緊張,那不是別人的屍體,是您自己的。”那舵手也歡然應聲說道﹕“這屍體是你自己的,你該知道喜樂﹗”
原文的活力,在於重複那兩個簡單的字“是你”。如果覺得那重複乏味,改成只有兩人在說話,我以為是把整段給糟蹋了。第二點要注意的是那渡者說﹕“可賀”,他用的是日常道喜的話,像人遇到一個官員升遷等喜事所用的,竟出人意表的用到三藏的褪卸凡體而升證佛果。海倫赫斯譯作“你該知道喜樂,”太遠離常套(對話必須合於口語),從來沒有人用那種方式跟人說話的。
這裏引到了語態的問題。當翻譯散文體對話的時候,應該使人物說話合於譯文思路。應該聽到他們的語聲,就像小說家聽到他塑造的人物談話,那聲音是顯明而真確的。但翻譯的人,無論是譯東方,或歐洲語文,似乎多不照這原則去作。
且以碧翠蘭耐(Beatrice Lane)所譯的日本“能”劇土雲為例。一個名叫小蝶的侍妾的對話,被譯成﹕“領了醫生所給的藥,我,小蝶,已經來到了。求如此告訴他。”你可曾聽到任何人這樣說話嗎﹖準確的翻譯應該是﹕“請稟報大人,小蝶從侍醫長那裏給他送藥來了。”
此類翻譯的洋涇濱,並不需要文學天才才可避免,只需要簡單的養成聽辨談話語態的習慣就成了。不能夠參閱原文的讀者,自然會涉想到,這類古怪譯文,是由於譯者可佩的力求對原作的語態精確,以為得以直參作者的思想而自慰。甚至有人對我說,好讀的譯文,不可能傳達原文的真意。實際上,就上例來說,如果把這古怪譯文跟原作對照,就會發現,那全然是在武斷的作怪,毫不表示原本的語風。事實上,在表現自己思想時寫得極好的人(除非他在某種程度上習於翻譯),往往在面對外文原本時,全然失去正常的表達能力。我曾經審編過一本書,由幾位考古學家翻譯德國同行的文章﹔所有的譯者在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都是傑出的作家,所譯的材料,完全是技術性的和具體性的,譯者都能確切了解﹔但他們每一個都譯得一無是處,只是極可憐的洋涇濱翻譯出品﹔面對德文語句,使他們全然走調離轍。
我用“習於翻譯”的語辭,因為我相信,即使翻譯文學作品(不僅資料),也有甚多可以學習的。一個譯者,終究不必須是創作天才。譯者的身分,就像是音樂演奏者,不是作曲家。他必須對字句和韻律具有起碼的感覺力。但我相信,這種感覺力,可以極大的激發並增進,正像音樂的感覺力,明顯的可以這樣作。
一位我所仰慕的法國學者,最近在論到翻譯者的時候,寫道﹕“他們應該隱沒在原作的後面,讓原作真箇被了解,讓原作自己說話。”除了在罕有的淺白具象陳述語例(如﹕“貓追老鼠”)之外,很不容易在另一種語文中,找得到字字對等的語詞。這樣,翻譯變成了在不同的語詞裏面,選擇最近似的。例如﹕在英文我們不能說“讓他們隱沒在原作的後面”,大致應該說﹕“他們應該隱沒自己,讓原作說話。”諸如此類,我常常發現,我要自己說話,而不是原作。我曾千番百次面對着原作,完全了解它的意思,只是不知該如何重新煉鑄成譯文﹕不僅要具有正確的字典意義,還要有原文的強調,語氣,和辯力。
不過,那位法國學者又說﹕“只講究美感,會失去翻譯的真實。”我寧願說,翻譯者的真實功夫,是從“講究美感”開始。在此之前,外文知識自然是必要的根基,但那是屬於語文學的範圍,與我所討論的翻譯藝術無關。當然,有些作品只表現邏輯意義,不關感情。但特別在東方,是絕無僅有。甚至在哲學作品中,也經常訴之於情感多於邏輯。當我譯中文詩約六年之後,僅憑本能的引導,發現我自己無意的順從一種規律﹕把[譯文]重音放在每一個中文字音上,重讀的語音自合符節。例如在
深山無人徑
甚至可以把多至三個的輕音節來分開重音,像在
依然弄扁舟。
這會給予我們一種感覺,就好像是賀浦金(Gerard Manley Hopkins)所說的,“鬆弛韻律”(未經複案)。我未用韻腳。因為我想,湊合韻腳,會把譯文帶得遠離原作。但在每行末一字的恰當選用,同樣重要,雖不押韻,仍等於使用韻腳。在自由詩體中,各行間的音韻關係,其重要性不減於傳統的標準韻節。雖然如湊韻的詩匠們,有時確實搞到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一位譯者(姑隱其名)譯了以下二行詩﹕
那個小孫,十二歲減五,
不能紡線也不會深掘土。
信不信由你,原作所說的只是
兒女不知耕績苦。
同時,雖然這位譯者搞得一團糟,不過我不懷疑他該用韻腳,因為此君身經親歷的是寫押韻詩。翻譯的人必須選用他得心應手的工具。這叫我想起林紓(琴南)的話。這位翻譯大家,曾把許多歐洲小說譯成中文。當有人問他,為何用古典文言譯迭更斯的作品,而不用今體白話文的時侯,他回答說﹕“因為我所擅場的是古文。”
從這位特出人物的故事,我們實在可以學習很多翻譯的功課。我願用些篇幅來討論。讓我來引述他所譯孝女耐兒傳的序文,作為引論﹕
余嘗臥病,獨處室內數旬。經日家人往來,穿戶過室,步履雜沓可聞。余雖不見其面目,聞聲可知過我室者其誰。余有數友,時挈西書過我,譯述朗誦於予。予雖不諳西文,然習聞可辨其文體正確不爽,猶識辨家人之履聲也。
林紓(1852-1924)本來是以論評作家著名。他的古體文,文體簡潔清新而有力。他的從事翻譯,多少是偶然的。在1893年,一位年輕朋友王子仁剛從法國留學歸國,帶來一本大仲馬的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用日常的白話口語傳譯給他﹔林紓就開始轉譯成文言文。這似是件頗不尋常的事。因為雖然有些中國短篇傳奇是用文言寫的,但小說從無例外的是白話體。譯文刊行後,極為成功。
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他有大約一百六十種譯作問世。他對王子仁極為愛戴,但並未再合作翻譯。王似乎早亡。但王有兩個懂法文的姪兒,跟林合作翻譯了幾種作品。在二十年後,其中之一曾幫助林翻譯貝納丁(Beranrdin de Siant-Pierre)的保祿與維琴尼。在從事翻譯約二十五年的時間,他至少用了十六個翻譯同工。這些人多是年輕有為,曾受過高深教育,被送到海外,學習海事工程等實用學科,他們不久就專注於外交或政府生涯,自然不能長久跟林同勞於譯事。
當然,林紓的譯作方式有其缺點。在“門外步聲”的比喻中,或多或少的承認,他的不懂外文,有些像瞎子入畫廊﹔朋友們可以告訴他,關於圖畫的一切情事,除了實在的景象如何。自然這種譯法,會引致細節上的誤意﹔他不斷的收到從全中國各地讀者寄來的正誤表。使他成為一個卓越翻譯家的因素,是他極有力和生動的文體,和對傳達給他的故事的強烈感受。在他所譯容琪(Charlotte Mary Yonge)的大鷹與鴿子序文中,他寫道﹕“書中人物立刻化為予之至近至親。彼陷困窘,予亦失望﹔彼遇成功,予亦得意。予似不復為生人,第傀儡隨着者之牽引而已。”
他的翻譯極為迅速。在1907年中,他發表的譯作有司各脫的 The Talison 和 The Betrothed;迭更斯的孝女耐兒傳,和滑稽外史﹔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拊掌錄﹔有馬禮遜(Arthur Morrison)的The Hole in the Wall還加上道爾(Conan Dole)及其他通俗作家所寫的一些故事。
他最著名的翻譯作品,大概是迭更斯的小說。他翻譯了迭更斯所有的主要創作。我曾經把一些譯文段節來跟原作對照,從表面上看來,他把迭更斯的作品譯成古典文言文,似乎有些古怪﹔不可避免的,迭更斯變成了另外一個作家。在我的印象中,是成了一個更好的作家。他的過度修飾,誇張渲染和冗贅絮聒的文弊消失了﹔原作的風趣仍在,但轉變成一種精密簡潔的風格。每一處迭更斯偏於豐肥繁茂的敗筆,林紓都使其成為優雅而有力。
在這點上,你會懷疑林紓是否該算為一個譯者。但就他所譯的迭更斯小說而論,從任何程度來看,都不該指為“述意”或“改編”。無論如何,他是個傳導者,把歐西小說,最大量的介紹到中國。中國小說久停滯在說古書的風格,不復為當代小說所樂用,藉着林紓,得以振墮起衰,重獲生機。
說過從林紓的成就所學的功課。首先,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譯者,都必須以文為樂。我要舉的另一個例子,是艾克頓(Harold Acton)與李義西合作翻譯警世四故事,他們很像林紓跟他的翻譯同工間的合作方法,成品有多大的差別﹗
譯者的古典或今代風格,並無多大關係。有的作家,自幼受聖經薰陶,使用聖經體的風格,自得心應手。我要說到魯斯(Gordon Luce)的緬甸皇朝琉璃宮紀史。他刻意經營前後一致的古典譯文,和翻譯劣手無原則的間雜經文語調(例如﹕“這兩個”寫成“者雙”),實有天壤之別。
第二點,要考慮選些甚麼書來譯。約在1910年,小說家兼翻譯家曾樸,往北京訪林紓,向林解釋,他的譯作,只不過是在汗牛充棟的唐代傳奇中,加上些洋材料,製造的新唐傳奇。曾樸說,這種作法,對於中國文學前途,並無足輕重。他建議林紓,列出一些傑作,依年代,國別,文學宗派編選,然後照次序有系統的逐一翻譯。林紓解釋說,他自己不懂洋文,無法開定如此一張清單﹔除了照他既有的方法以外不知別途﹔他的朋友們帶給他的書都是名著,他想,也無需有一個預定的次序。
看來曾樸在此以前不曾見過林紓。如果知道一點林紓的個性,他會知道按日程行事翻譯,對林某來說是不可思議的。而且照我所知,林紓從事翻譯的主因是他喜愛譯事,絕不曾着意於影響“中國文學前途”,雖則他豐富的譯述生平,改革了中國小說。
說到節目和程序的價值,這又是個顯然的問題。文化宣傳成為一部分人的新注意點。一些政府資助的機構,忙着開列一些必需翻譯的作品名單﹔一群年輕小伙子,粗通語文知識,但常是毫無文學才華,被牽來從事翻譯。他們對所作的,全無特殊熱誠,唯一吸引他們注意的是躋身官定“名著”翻譯榜。我有一種感覺,這種制度不會多麼順利。關鍵在於譯者必須對其所譯作品感到興奮,為之日夜思維,感覺必須把它譯成本國文字,激動到一種程度,必待譯作完成而後方得安息。“名著”未必恒常是名著,可能隨時息其著名。也許得列名著之林,是因為各種外在的和比較臨時的因素。說來似是不久之前,我童年時讀過一首題為“開始拔錨”的詩,算為“名作”,必須得背誦它。也許,有一天,那首詩會再復著名,亦未可知。但在此時,讓譯者博覽慎選,找他自己感覺興奮而渴想着筆翻譯的作品,如果今天還未被列為“名著”,很可能在明天。
日本人的信念,寄於由委員會集體翻譯。最古的日本文選萬葉集英譯,似乎是二十人分工合譯(內中只有一個非日人),在1940年譯竣出版。結果極為優越。但我確信,事實上這得歸功於那唯一的西洋人賀奇生(Ralph Hodgson),在譯工的最後階段,顯然是授權他自由裁奪。叢書的次一種是日本“能”劇(1954年出版),似是由十八人執筆﹔但可確知沒有賀奇生那樣的西洋詩人,如我推想在譯前集時的那樣便宜行事。結果,劇中的抒情部分,簡直全成了散文,武斷的分行刊印,當作詩體:
在這幾年來
我過了一個村居生活。
日本文學由外人主譯,使日本委員會感到“遺憾”。適得其反,我相信,幾乎經常是譯者寫出他自己的語文比較好些。譯者並不可能善於運用另一種外文的所有智源,詞彙已難以應付,講到韻律,幾乎可以確定準會一敗塗地。
這篇譯事散論主要的是談到東方,因為那是我自己經驗所在。但我所說的,幾乎全都同樣適用於歐洲語文。我恐怕有點兒自命唯我獨醒的態度。我對一些別人的譯文挑剔毛病,有時還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認為那是出乎自然,各人都是偏愛他自己的作品。譯者終究是使譯作適合自己的口味和感覺力,自然喜歡自己的譯文過於別人的,正像他喜歡穿自己的鞋來走路一樣。![]()
注:引文係自英譯。
原作者韋列(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