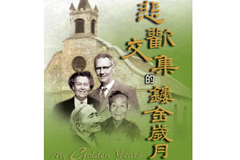我曾住過模里西斯島

在香港度過了四個不很安定的年頭以後,我便決心移民到模里西斯島(Mauritius)。這是五十年前的事。
搭香港開往巴西的荷輪,路經馬尼拉和星加坡,兩埠各停四五天,觀光,訪友,船上有游泳池和中國飯可吃,同房間的是中國人,我自己又不暈船,一路二十多天,便在很愉快的氣氛中度過了。事隔雖久,但是舊日經歷,仍時縈腦際,對於曾住過僅十六個月地處印度洋中心的小島,依舊懷念不已。
模島寬約十五哩,長約二十五哩。那時,人口不足五十萬,蔗糖是主要的出產,年產約五十萬噸。2004年,人口已經到了一百二十萬,生產竟追不及人口上升的程度。幸而戰後糖價節節上揚。各大洲的航空線都伸展到模島來,以那終年溫和的氣候,令人沉醉且不曾污染的環島海濱,和那秀麗,熱情奔放的混血兒女們,使觀光客們流連忘返,拋下了模島所需要的外匯。此外模島出產紅茶,加上近年來由香港,日,法,印,美,湧進工業的投資,開拓了很多就業的機會,增加了社會安定的因素。罪犯除了有升天入地的本領,環島皆是波濤洶湧的大洋,難逃法網。

中國移民始於百餘年前,初時來自馬來亞和爪哇,其中以南順人(南海和順德)移民最早,後來梅縣的客家人移民漸多,商人便供多於求,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再加上習慣和言語的隔閡,不幸兩集團時生齟鼯。接着南順人便開始在附近的馬島(Madagascar)開拓,後來使馬島成了南順人“獨佔”的局面,排擠客家人。但有一戶客家則屬例外,那是留法讀軍事的黃強將軍。淞滬抗日時,他擔任享譽中外十九路軍的參謀。第二次大戰後,曾代表中國參加在越南的授降典禮。當時的越南總督,後來調到馬島做了總督;因黃強與他有舊誼,南順人卻難為他不得,於是他成了僅有的一戶客家移民。我與他有一面之識,他曾親口道及此事。
今日模島的華僑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三,除了在路易港營商者外,其餘散居於大小不同的十餘個村鎮,與糖廠附近之鄉區。模島之食品和雜貨業久已操在華僑手中。我曾將模島華僑與美國佔有百分之三的猶太裔的成就相比,只是有小局面和大局面之別而已:工業,各市鎮房屋的投資,政府各部門的公務員,部長,法官,醫生,律師等。其中最傑出的為朱梅麟,三十多歲時,已被英殖民政府委為議員;獨立後,成了民選議員,今日兼行政部長,近年於刷新政治,排解華僑間的糾紛,並爭取外資,振興工業等不遺餘力,其他政蹟昭然,有口皆碑,是模島政壇上三十年來唯一的不倒翁。二十多年來,我與他只通訊兩次,但他予我印像至深—面上永遠堆着笑容,樂於指導新移民,有高度的判斷加和智慧,溫厚和有分寸的談論…廣東梅縣是個文化和教育很發達的縣份。模島華僑在戰前,即使是個小食品商,也將子弟送到家鄉去讀書。在我所相識的模島華僑中,大半寫得一筆好字,並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很深的薰陶。模島,如同印度一樣,各為英國統治一百五十多年。島上流行法語是英法協定的結果。
我未曾讀過法語,在去模島以前恐怕登岸之後見了人要瞠目結舌如同聾啞,所以在香港臨時拜師學習。法語文法有似日語處,表達“時態”困難,再加上不規則的“名物字”的雌雄性,非下強記工不可。過了多年,在遊巴黎的時候,我的法語還可勉強派用場。在巴黎,只要稍得講法語,足可化冷冰面孔成笑容,與陌生人交成朋友。法國人沒有英國式的民族優越感,很易相與。“綁揪!摸鬚兒,捨利無不來?”(早安!先生,你可以嗎?…)接着改用英語解釋你的法語不夠用表示抱歉,並將你的問題說出來。巴黎人大都懂英語,但講不好,也有不肯講的。你用英語他用法語,兩人指手劃腳,總可搞個明白。不然,只裝懂了,臨別道一聲;“唯,唯”“明兒謝不顧”(是,是,多謝!)皆大歡喜。
法國人不喜歡講英語,我認為沒有理由怪責他們:英法兩國打仗自“聖女貞德”那時為始,至拿破崙在滑鐵盧的敗仗為止,其間時打時停,在歐洲足足爭執了三百年。在美國獨立以前,北美洲北方的法軍聯合“紅番”擾南部的英移民,致移民和英軍北上報復,至終英軍政佔駐魁北克。“巴黎協定”遂迫法國讓出俄亥奧河流域予英,英法在北美洲的爭奪,才暫時告一段落。

模島當時也曾為英法兩國爭執的一部分。模島本為葡人發見,係一無人煙之荒島。約一世紀後,荷人移爪哇的土著,於此種植甘蔗。四十年後,颶風過境,人物蕩然。後來由法國佔領。法大革命時代,貴族出亡,有以模島為避難地的。等到英殖民印度,以模島為基地的法軍,干擾印度和南非間的航路。在蘇彝士運河尚未開鑿的時代,模島的重要性可以想見。英國謀一勞永逸計,傾海軍全力進攻模島。法軍遂接收“光榮投降”的條件:法移民保持土地權,維持法國語言,和天主教學校繼續受政府津貼等。模島混血人中,凡遇添丁之喜時,親友每先發問:孩兒的皮膚是甚麼顏色?知道男女性別倒屬次要。
模島混血人中,含有法,非,爪哇及印的成分多少不等。自印度來移民,以印度教人最早,回教人較遲,也較少數,各不通婚。華僑與印度人通婚者少,但與混血人者卻有。
法國人習於浪漫,早於法文學名著中反映出來,我們所識的有“茶花女”,“娜娜”和作曲家蕭邦的情人喬治桑一生的事蹟等。模島法裔人也未例外。他們之間的一些浪漫生活,是我前所未聞的。我想垃圾到處有,在此不值一述了!
模島一望無際的蔗田,全屬糖廠所有:英人一間,政府營一間,其他十九間為法移民所營。華人只有向工商或專門職業上發展。近年“非洲團結組織”,曾在模島開會。不久後,“英聯邦集團”也在模島開會。此島的重要性,似乎與年俱增了!
模島設農業專門學校及大學各一所,分商,法,工,文各系。唯凡出國深造的青年,大都由於本島出路狹窄,在學成以後,便在國外謀久居之計了。此情在華僑中尤甚。
模島人對於古典音樂和歌劇,有高度的欣賞力。莎士比亞戲劇在模島各學校和青年團體之間時常有精彩的演出。那座近二百年歷史的歌劇院,是觀光客必到之處。其他名勝如島東部漁港的歷史博物館,西南部鄰近海邊一處山地的五彩泥層,路易港東去三哩的植物園,水池中生有特種水蓮,葉大如中國餐館習用之圓桌,邊沿向上捲起,是我在世界各處未曾見到的。
路易港是首府所在地,是模島唯一國際港口。其餘環島各地非有暗礁便有淺灘,不宜巨輪停泊。環島仍有英政府委任象徵式的總督,但實權仍操於民選執政黨(工黨)的總裁總理手中。對外政策中立,經濟至上,各國遠洋漁船,給油,上水,或搶修,無不歡迎。台灣遠洋漁輪多艘,目前仍以模島為補給站。前台灣曾派有農耕隊在此,於五年期滿後返台。繼之者中共派出農技人員。中國與模建交後,已提供約等值於三百萬美金的新飛機場援助。
 |
我到了模島,便租屋於島中央拔海一千八百呎的鳩比鎮。屋是木造的,法式,全部白色,四圍有草坪和花圃。那時正是南半球的冬日,每當斜風細雨之日,只罩一件雨衣便可禦寒。瀟瀟夜雨,不管打在屋頂的木瓦,或窗前的香蕉樹,都足引起我無限鄉愁來。
那時的鳩比鎮,人口不足萬人,以白人居多。鎮中心十字大街的兩旁有學校,教堂,銀行,郵局,商店,市場,有歐洲鄉下村鎮的模樣。附近有一所沈睡已久的火山,山口的邊沿造了一條公路,由此可俯視模島的大部分。山下的四週有數不盡的住宅,綠白相間,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給人以寧靜的感覺。鳩比鎮臥在山腳下。
冬盡春至,我們一家五口,於短短六年內,在模島作了第三次的團聚。難為了的是孩子們,在呀呀學語後不久,就學台語,接着粵語,今又要學法語。親人別後團聚,該是人生至大樂事。我們一同去參加國語禮拜;一同去看公園的玫瑰和荷花;看附近隱藏於橡樹和樟腦樹林中的法式古老庭院,住宅;看小橋,流水,游鴨,煙雨中的山村人家,和渡低迴的小湖。到了春光明媚的日子,沿着山路去看谷中出沒的麋鹿。夏天,也曾在蕉風椰雨的海邊游泳,拾蚌殼,和到附近的山邊摘野草莓,更在路邊的小溪中,撈魚蝦和水草。我最愛那掠過山巔柳絮似的白雲,和金色斜陽下的彩虹和陣雨。仰見頭頂不遠處的雲,只有巴掌那麼大。等到晴空萬里,菊黃蟹肥的秋日,我們同去採荔枝和桂圓,或者到島中央的林山地區,去採山薈。…
我們的商店開業了。但我未曾以模島那樣悠閒和安定的環境感到滿足。非洲大陸對於我還是十分神秘的,加上我有重作工業的心願,不久,我又匆匆地向非洲而去。
過了一年多,一家人在模里西斯那邊,又再次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