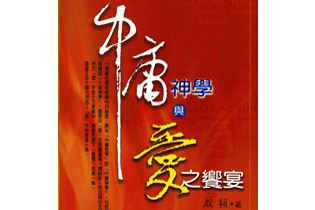法國煙雲南北路(下)
“From Bordeaux to Giverny”

女詩人Camille Cassorla對法國第七大城市,大西洋岸最大港口,河邊古城波爾多(Bordeaux)有如許頌讚:
波爾多呀!我多麼冀望深切地了解你,
探摸着你的脈搏,生活在你的旋律中,享受着你的情懷。
當我橫越你的方場,在你窄窄的街道內徘徊,在你古舊莊嚴的樓宇前沉思,
你展開淡淡的歡容,慎重地啟示你的魅力和神秘。
我要在你的餐桌前淺斟低酌,在你的櫥窗前依戀,
在你的園林內漫步,日以繼夜地讓我的五官沉醉在你的聲色中。
我終於明白了,你冷眼地望着走過你面前的人群,
正如你凝視着流經市內河中的滾滾濁浪。
Bordeaux建城於公元前三世紀,是古國阿基坦(Aquitaine)的首都。1152年英王Henry II迎娶法王Louis VII離了婚的妻子Eleanor of Aquitaine,Bordeaux遂成為英國的屬土。這從古以來釀酒佳地便成了供應倫敦的酒源;酒的航運促使它成為大西洋岸的名港。英法百年戰爭後,英國的勢力被逐出,Bordeaux回歸法國懷抱。十八世紀此城大興土木,建造了很多美輪美奐的樓宇,建築家譽它市容的美觀僅次於巴黎。出類拔萃的有市中心的劇場 le Grand Theatre。這巨型建築屋頂側有一條長長的門廊;十二支柱上分別雕刻了十二位不同姿態的音樂女神。我在那陰暗得使我不寒而慄的St. Andre大教堂(其深度可比巴黎聖母院)看到一非常恐怖的油畫;有兩人受鞭笞酷刑,背後籬笆上掛着三個人頭,頸中的鮮血沿着籬笆滴到地上,草也被染紅了。此畫怖厲的場面深銘腦海,久久驅之不去,可以反映此城血腥的歷史。

le Grand Theatre, Bordeaux

St. Andre Cathedral, Bordeaux

Esplanade des Quinconces東面大噴泉
離教堂不遠的方場Place Gambetta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斷頭台的所在地;三百人在此丟掉了頭顱,包括神父,賣酒商人,貴族,文人等,大多數都是枉死者。處決那三百年望族,簪纓之後的前市長兼大慈善家七十四歲老人Count Joseph de Fumel後激起公憤,方中止了這慘烈的屠殺。現在斷頭台舊址建了一英國式的花園,當年血跡已洗滌淨盡。Bordeaux最大的廣場是Esplanade des Quinconces,亦是全歐洲最大的。東面大噴泉是一組雕刻系列,代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象徵。刻着“正義”,“平等”,“友愛”的口號。噴泉中央是一圓柱,頂端站着一有翼天使,是紀念在恐怖時期(1793-1795)被酷吏Robespiene送上斷頭台的Girandists全部黨人,西面臨Garonne河有兩支圓石柱,是“通商”和“航海”,代表此城的精神。彼時太陽西下,夕照反映在河面,金光耀目。Bordeaux的古蹟,處處透示出盛衰興亡,慨嘆之餘,吟出“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

St. Emilion

修道院 Cloister
離Bordeaux東僅三十五公里的中世紀城堡。St. Emilion是產酒名鄉。淡灰色的舊屋沿着小丘陵的斜坡密密地排列。我們早上九時許到達這小鎮的小方場。四邊滿設檔口,我向一小販買了幾罐鵝肝;這也是本地名產。城堡得名於隱士Emilion,他在八世紀鑿石營穴而居,後來在他的居處建了一所寺院,傳說不孕婦人來此求子頗有靈驗。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們只能參觀一十二世紀教堂,背後的修道院(Cloister)幽靜極了。大有“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的氣氛。時院內舉行畫展,領隊Bart認為破壞了和諧的整體;我認為不妨,名畫可為河山增點色彩。院後是城堡的邊緣,我可憑欄俯望殘破的舊城牆和城壕。離開St. Emilion,我們隨着Dordogne河,溯流而上,闖進河谷腹地。

Dordogne河谷
我們現在很難想像到這寧謐的Dordogne河谷是英法百年戰爭的前線,山明水秀之鄉是當年血肉橫飛的屠場。十四世紀時,鄰近的Bordeaux是英國的城市;我們便明白這裏的干戈不息了。戰爭緣起於1337年,法國王座沒有直系的男性繼承人。英王以母族近親,不客氣地取法國冠冕加給自己頭上。法人不甘受英王統治,從疏遠的王族中另立一君,於是開始了這百年浩劫的爭奪戰。戰事結束於1453年,聖女貞德(St. Joan of Arc)擁立Charles VII,鼓舞法國軍民眾志成城,擊潰英軍,恢復全部失地。在這清澈流水兩邊,矗立了很多堡壘,一邊屬英國,另一邊屬法國。當一方建一堡壘以窺敵情,另一方必在隔河築防作針鋒相對,在寸土必爭的持久戰中是有此必要的。歷史籠統稱此為英法之戰,實情是複雜得多,在封建制度下,王對下的是侯,然後是守土官,然後是兵士和佃戶。效忠的對象並非永遠一線不動,為着個人的利益,在中層或下層階級時有變動效忠的對象。

Beynac堡壘
我們參觀的Beynac堡壘,名義上屬法國,其實是地方政治,權力,和獨立的象徵。只能說在百年戰爭大部分時間,守此堡壘的將士效忠於法王罷。Beynac形勢險要,處於一峻峭的懸崖上,遙遠望去金黃色的牆壁似是金黃色巖石的延續。在城樓上俯望,Dordogne河了然入目,不單止是岸邊原野行軍,甚至順流而下的舟楫也偵察得很清晰。
除了堡壘外,河谷還有很多引人入勝的景物。建於挺立在岸邊危崖的山城La Roque-Gageac,樓宇像級田般重重疊疊,層次井然。Dordogne河流域有很多洞穴,裏內有原始人留下的壁壘。我們午餐小息去處是Les Eyzies毗鄰這些洞穴,村內有一頗有名氣的博物館,解說河谷盤古時代的情況。我因時間不充裕,沒有進去參觀,只在大街買了一客三文治,一瓶橙汁,漫步走向河邊密林處,坐在草地上悠閒野餐,別饒詩情畫意。

挺立在岸邊危崖的山城 La Roque-Gageac

小鎮Brive市內大教堂St. Martin
晚上投宿於小鎮Brive。城市設計像一蜘蛛網:一組同一軸心而不同直徑的大圓圈作主要街道,又有多條街道從軸心幅射出來至各方。市內有一大教堂St. Martin,座於軸心正中。剛巧那時市政府大廳展覽中國山水畫,在法國碰上故國文物,確是難得機緣。旅館位於最外的大圓圈的街道上,是莊園式。居室面積很大,除了睡房,還有書室(備有檯椅),會客廳(備有沙發,咖啡座,和電視),浴室有一大浴缸,和洗手間分隔開。是夜晚飯是燭光影照下的地方風味餐。餐室一角有一鋼琴家和小提琴家合奏古典音樂作背景,生活藝術,能越此乎?飽餐後出來散步,街道靜如止水,不見人影。涼風習習,繁星拱月,真是“殘曙微星當戶沒,澹煙斜月照樓底。”
早餐後,我們向Dordogne河流告別,上午在瓷都Limoge流連了一個鐘頭,參觀了一製造瓷具廠。此地出的袖珍盒子,色澤光艷,造型小巧,設計新穎,素來為收藏家的獵物。我見到一盒子上面站着一白天鵝,拿來一看,愛得不忍釋手,於是買下來。誰知挑起了我的收藏慾,回家後又多買了八個。午餐後遊覽車開入Loire河流域。河谷地區點滿了文藝復興時代王室和貴族營建的別墅(Chateau),豪華瑰麗,飲譽人間。遊覽團選擇了Chenonceau為參觀對象。此別墅是法王Henry II在十六世紀中(1546)贈給他的情婦Diane de Poitiers的。為了明瞭此別墅的背景,我有對這風華絕世的一代尤物作一簡短的介紹必要。

Diane de Poitiers

Catherine de Medici
1514年Diane十五歲時下嫁給Normandy的省長Louis de Breze,誕下兩名女兒。1522年她的父親涉嫌參加作反集團瑯璫入獄,被判死刑。她為營救父親,多番設法私下和法王Francis I會面。Francis I稟性風流,愛拈花惹草,用一紙赦令買取和Diane的一夜溫存。從此她和法國王室攀上了曖昧的關係。1531年丈夫去世,她索性搬入了Francis的離宮,成為御駕隨行隊伍中一要員,她喜愛穿黑衣作哀悼亡夫,配上金色的頭髮,更使她艷光四射,成了宮庭內眾所周知的風流寡婦。Francis委任她為太子的導師,改善太子的儀態,那時她已進入三十六歲的狼虎之年,而太子僅是血氣方剛的十六歲小子,兼授房中術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在Diane的薰陶下,太子從一位沉默膽小的青年蛻變成為尊嚴穩重的法王Henry II。他沉迷於Diane的魅惑,把王后Catherine de Medici冷落了。那時的女人老得很快,三十五歲後牙齒開始脫落,面上顯出皺紋,身段轉癡肥,而Diane呢?因為她戒吃甜品,節制食量,每晨必作騎馬運動,勤於沐浴(那時代人稀有此習慣),年屆五十,青春長駐,身段保持得很窈窕,皮膚仍滑嫩,前胸挺起,步伐婀娜。頭髮雖有少許灰白,但她衣着仍以黑白二色為主,不多加修飾,更顯出成熟的風韻。她很明白自己的身分,Henry II苦纏着她,她倒勸法王和王后燕好。Catherine因此生下六兒女為王室傳宗。當王后患了猩紅熱症,Diane呵護在旁,細心調理直至王后復原。王后和她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Catherine常對人誇耀:“世間女人很少像我,愛屋及烏,愛丈夫而及丈夫的情婦。”Chateau Chenonceau是Henry II對Diane示愛的禮物。Diane成為別墅的主人,大加修飾,增設園林,今天我們還可隱約看到這一代名女人的手筆。Henry II在三十八歲的英年和部屬武士比作比武遊戲,不幸被長矛刺傷眼睛,不治去世。那時Catherine de Medici方露出猙獰面目,將Diane從Chenonceau逐出。Diane行年五十八,黯然返回舊居。絢爛的生涯轉歸平淡,默默地終其餘生。這是一段很富傳奇色彩的愛情故事。


Chateau Chenonceau
我在雲霧繚繞那天,來到Chenonceau前。我見到一座古堡遊離地在Cher河的銀色水面裊裊升出。這是童話世界的幻想啊!在這巨形建築物的四角,矗立着四座尖塔,圍繞着這別墅是修理得很整齊的園林,面積廣袤,一望無際。別墅的特徵是那橫跨Cher河的三層高長廊,在陰雲密佈的一天,黑黝黝的河水宛若城壕的大渠,保衛着雪白的古堡。在陽光明媚的日子,河水變成了一泓銀池,反映着整座古堡,在水中浮動。別墅內有很多廳房,掛滿了綿繡織氈,牆上釘着很多油畫,其中有些是Diane de Poitiers和Catherine de Medici的肖像,好像告訴我們十六世紀的別墅主人尚未離開人間。我行到那跨越Cher河的長廊,兩邊擺了好幾盆葵類植物,地面是鑽石形的雲石,黑白兩色的合砌。大玻璃窗外河邊的花樹湧進眼簾,室內外景物在此渾成一體。突然空間響起文藝復興時代的音樂,長廊內有數對男女遊客,竟翩翩起舞。我彷彿參與了十六世紀的豪門盛宴。長廊是Diane de Potiers設計的。

Clos-Luce別墅
我們離開Chenonceau,北行抵達Loire河岸。Tierry將車子在Amboise市隔河北岸空地上停下來。Bart解說:“河的對岸是Clos-Luce別墅,是文藝復興時意大利名畫家Leonardo da Vinci晚年隱居之處。Francis I請他來法國居留以振興藝術頹風。他晚年有很多傑作,現陳列在別墅改成的博物館內。你們站在河邊能清楚地看到這博物館。河邊有da Vinci坐着的巨型石像。傳說人們若在石像的膝頭坐上五秒鐘,一定找到如意的愛情。黃昏時市民帶了他們的愛犬在河邊草地上嬉戲,所以草叢暗伏了很多機關,你們步履分外小心,若將臭氣帶回車子,將成了全團的罪人。”話剛完,有人在車後大聲地說:“若找不到愛情,先踩來一腳狗屎,豈不是糟糕。”全車人大笑,團友排隊輪流坐在da Vinci的膝上拍照。我察覺到這石像是裸體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文藝前鋒竟露出不文之物,確是人生一大諷刺。當晚留宿在Tour市一旅館,我們要早些兒休息,翌日有很豐富的節目。此旅行有點像唐詩形容的:“曉發獨辭殘月店,暮程遙宿隔雲村。”

Mont St. Michel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
這是我首次從海邊看到Mont St. Michel的印象。這位於法國西北,在Brittany和Normandy邊界上的大西洋海島,是最寶貴的全人類文化遺產之一。“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大西洋上空時常刮風,此島終年被一層薄霧蜃氣縈繞着;島的四周白浪洶湧,好像海潮要將它吞下去般。這情景給Mont St. Michel加了一張神秘的面紗,產生了不可抗拒的魔力。島上的寺院自八世紀以來已經歷了千多年的風雨,目睹人間無數的政治浪潮。十二和十三世紀Benedictine僧旅駐足此地,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香客;他們行經千山萬水,歷盡九磨十難,好不容易抵島上的寺院。最危險的是島和大陸間不可測的流沙和無定期的潮汛。很多香客都在此陸沉或淹沒,命喪他鄉。香客的生活是很艱辛貧苦的。沿途沒有衛生設備,一路上風餐露宿,拾取些殘羹剩餚充飢,除了身上襤褸衣服和腰帶內些許銅幣外,便一無所有了。他們所到之處,既受人的尊敬,又給人恐懼。因為長期流浪街頭,一定帶來可怕的疾病,是疫症的源頭。能安全踏足St. Michel島上的,為數甚少。最可憐的是那批未足十五歲的兒童香客。很多是貧家子離家冒險,有些是父母送他出外祈福,保佑家鄉免於兵革或疫症的災難,有些是貴族或富有商人的子女,因家庭環境複雜,憤而出走,義無反顧。他們離家時都滿懷興奮,抱着幻想。路未走及十分之一,很多兒童被人拐賣去了;男的送到遠處作奴役,女的被陷落妓寨。其餘的或被捲入地方鬥爭慘被屠殺,或因飢寒疾病,倒斃街頭。能回故鄉,重睹雙親慈顏的,萬中無一。我們這些二十一世紀的遊客幸運得多了,乘遊車跨越那人築的長堤,施施然直抵Mont St. Michel的邊緣。寺院的確是巍峨雄偉,名不虛傳。唯一的劫難是入門處前擺了一條長達半里的人龍。

Utah Beach
當天下午,我站在第二次大戰時聯軍在諾曼第(Normandy)海邊登陸的一部分Utah Beach上。這是美軍冒着鎗林彈雨搶灘處,我凝視着茫茫大海,有無限的感觸。海灘背後是些高地,當年德軍的炮火都安置在那裏;只有一紀念碑述及這扭轉世界大局的戰事。Saving Private Ryan電影內一幕幕血花飛濺,驅體糜碎的鏡頭浮現在腦海。美兵在毫無保障下以血肉之軀承當高地上堅城的利炮,這是人肉磨坊啊!據統計,諾曼第登陸戰陣亡的士兵超過十萬。聯軍統帥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因此一戰威名震天下,後來順利地登上美國總統寶座。“一將功成萬骨枯”此話不虛也。

陣亡美軍墳場 Colleville-sur-Mer
我們跟着參觀陣亡美軍墳場(Colleville-sur-Mer)。近入門處有一半圓形的樓座;樓身是一組長長的支柱。樓側石碑上刻着諾曼第登陸行軍地圖。拱形紀念廊的開朗處豎了二十二呎高的青銅碑;上面刻着“美國青年的靈魂在海浪上升起。”對着是一望無際的草地,上面插着一行行的十字架,這是陣亡兵卒的長眠地。墓碑平放在草地上,羅列得很有秩序。除了猶太裔插上大衛之星外,其餘墳墓全插上十字架。我徘徊其間,默默沉思。
煙雨凄迷,萬里名山凝血淚;
音容寂寞,一灣流水盡哀聲。
Bart述及一頗動人故事。1994年他領團到諾曼第陣亡美軍墳場,團中有七十多歲的Bryant夫婦請求他協助尋找Sergeant James Clarke的墳墓。原來五十年前Bryant是Sergeant Clarke同袍僚屬。在戎馬戰亂中,士卒同甘苦,二人遂成莫逆之交。諾曼第登陸戰時,Sergeant Clarke身受重傷,彌留時將手寫的遺書交給Bryant,囑咐他若有幸生還,回美國家鄉,親手交給他的妻子。Bryant戰後依言見到了Sergeant Clarke的遺孀,二人對這死難英雄的懷念產生了共鳴,因此結成夫婦。五十年來夫婦倆將此傷心往事隱埋在靈魂深處,直至現在為了紀念諾曼第登陸戰後五十年,首次蒞臨法國,要在Sergeant Clarke墓前弔祭致哀。Bart將此故事轉述給墓地管理人,他帶他們三人到Sergeant Clarke墳墓,且備有一桶濕泥隨行。管理人將泥倒在碑上,並用鏟稍作清理;碑上的雕名更為顯著。Bart為這涕淚縱橫的老夫婦在碑前合拍一照留念。
英軍紀念陣亡戰士墳場另有一番景象,設計比美軍的簡單得多。每墓都有一簇鮮花,碑上除了名字外,刻着警句一。例如:
在世界中,你是一個數目,在我心中,你是整個世界。
你為我們而死,將來我有為別人而死的機會嗎?
我們終有明白的一天。
這些警句確能啟人深思。

諾曼第戰區英軍紀念陣亡戰士墳場
離開諾曼第戰區,我抱着沉重的心情踏入小城Bayeux。這小城是一農業中心,有二千年的歷史,市內有法國各時期風格的建築。最珍貴的歷史遺物是一長達23呎,高達20吋的刺繡畫卷。這畫卷細微詳盡地繡出1066年William the Conqueror從諾曼第出師,橫渡英倫海峽,征服英國的戰爭Battle of Hastings。

William誕生於1027年,是諾曼第侯Robert the Devil的長子,他的表兄英王Edward I去世後,英國爆出內戰,Edward I遺命他繼承英國的王位。於是他起兵平亂,在Hastings他射殺僭取王位的Harold,登上倫敦的寶座。他駕崩於1087年。他在位時勵精圖治,隨行的Norman官員都是出色的行政人材。英國在他的任內,欣欣向榮,呈現出中興局面。從法國去的Normans和英國本地土著Saxons溶化後產生了後來的大英帝國。這畫卷是William的異母弟Bishop Odo委工匠群織成紀功的。恰在1077年Bayeux大教堂開門典禮時竣工。雖經歷了九百多年的歲月,羊毛原料仍保留鮮艷的彩澤。畫卷繪出中世紀的日常生活,民間傳說,和神話中的怪獸。手法頗類似現在的漫畫集,僭王Harold唇上有一小鬍子,眼睛時常轉動,儼然一奸雄扮相。William道貌岸然,凜凜大義,絕對是一英雄,我們帶着耳筒,聆聽英語解說,在畫卷前漫步一周。看罷畫卷,日已西沉,我們赴旅館晚飯,就在此地居停一夜。
 畫家Claude Monet |
次日遊覽車要在中午前開回巴黎,當天還有一很完美的尾聲。上午在小鎮Giverny小息,參觀了畫家Claude Monet(1840-1926)的故居。Monet享壽八十六歲,自1883年在此生活,直至1926年逝世。我們沿着一小徑穿過地底隧道進入花園,焦點是一狹長的荷塘,有一日本式的拱形小橋橫跨荷塘中心;小橋欄杆纏着紫藤花的葉條。四周植些垂柳,柔軟的枝彎彎地觸及水面,間中雜了些大杜鵑樹。塘邊還有涼亭和小徑,徑上蓋了被長青藤蔓鋪滿的木格子遮陰。塘中蓮葉蓬蓬,粉紅色的蓮蕊在墨綠叢中冒出。一小漁舟停泊在一邊,而一角呢?“留得殘荷聽雨聲”了。



Monet故居
Monet故居入門處有一畫室,是他生前畫巨畫荷花處,現改為出售關於他的書籍和他的畫影印本地方。有沙礫小徑引進他的二層高主樓,樓下廳內陳列了很多他的名畫抄本。原畫珍藏在法國各地博物館和畫廊內。我很容易地接受和欣賞他的傑作。他不像Chagall和Matisse,不屬於抽象派;我不用思索便辨出他畫的對象。睡房掛滿家庭照片和親友的畫,樓上展出日本友人尤其是畫家Hokusai和Hiroshige的贈品。其中一幅黃菊花且題有中文詩二句:“凌霜留晚節,殿歲競春華。”Bart見我在此畫前看得出神,苦苦要求我將此二句詩譯成英文;他可以共賞。他讀罷微笑點頭:“蠻有意思,尤其是送給Monet這八十多歲老翁。”
我最近讀了一篇寫得很好的巴黎遊記,但其中一些評論令我很不舒服。說“法國人稟性柔弱,自拿破崙後,從沒有打過勝仗。”我要講一句公道話,作者似乎沒有熟讀法國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兵士守着Verdun,抗拒德軍如狼似虎的凌厲攻勢。法軍拼死守着,和德軍展出戰壕拉鋸戰,歷時三年,德軍不能越雷池半步。法軍拼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決心,犧牲了三萬多青年的性命,國之精華,盡此一戰。Verdun的防衛戰,法國重創德軍元氣,算是打勝了。但此戰潰散了法國軍人的靈魂,震撼了民族精神的正義。當第二次大戰時德軍繞道荷蘭,比利時,包抄在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後攻陷巴黎,當年死守Verdun的名將Petain只好和希特拉作城下盟,雙手將法國奉上。寫到此處,這三篇共達二萬多字的法國遊記可以作一結束了,雖然還未包括巴黎。未知我螳臂之力,能駕馭寫巴黎遊記的載重車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