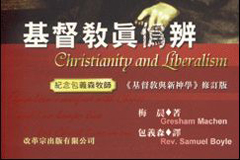華沙蘊藏着歷史哀傷

Praga
在1998年十月十七,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旅遊車載了我們一團二十多人離開假日旅店,沿着瀕河大道奔馳,左邊是華沙市區,右邊是威士杜拉河Vistula,是一片黑野,遙遠處點綴着些河彼岸Praga住宅區疏落燈火。我在車內思潮起伏:終於來到這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世界名都,名是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實只是五十多年前重建的新城。它雖是波蘭的首府,但滲入了很濃的俄羅斯和日耳曼文化,因為普魯士Prussia和俄國,在不同期間內,曾佔據華沙一段頗悠長的歲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毀滅了它的人口過半,使文化淪亡,宗廟丘墟。今天的華沙人是戰後從各地移民到來的子孫。他們的父祖在灰燼和廢堆中,建此新城。他們仍在尋找華沙的舊根源,摸索華沙的古幽靈。也許就是這矛盾,在世界名城中,給予華沙別具一格,散發出不可思議的魅力罷!
車子終於在河邊一空地停下來,我首先下車,涼風撲面,感到深秋肅殺的寒氣。仰望穹蒼,月明星稀。除了Vistula河的嗚咽流水和團友談話外,聽不到任何聲浪。我緊跟着領隊維也納人Dragan,華沙導遊Ludwig,和司機慕尼黑人Hans,踏進舖滿光滑圓石子的小街Bednarska,四條影子在前面向前溜動,直至一奶油色的樓宇前頓止。街燈發出微弱的黃光,攙和了月華,在這玉砌般的牆壁上,宛如塗了一層薄薄的金粉,門前掛着的銅牌GDANSK POD RETMENEM,更顯得璀璨,閃閃生輝了。被拋在後面的團友慢慢地雲集門前。我們魚貫步入餐館,未到大堂,早傳來管絃音樂,令人心醉,我們彷彿從曠野返回人間。

Vistula河日落
餐室非常寬敞,天花板很高,我立即聯想到四十年前電影“學生王子”中Heidelberg大學膳堂。那穿着黑色制服的侍應首領率我們坐在一可容三十人的長桌旁,我坐下環顧一瞥,長桌共有六張,另一角是私家餐室,亦坐滿了人。行人路對面是一列可供四至六人用的雅座。令我最注目的是一身型偉碩的小鬍子和他的妻子及兩位十多歲的兒子,他們笑容可掬,時投給我們友善的眼光。餐館前端是很長的低窪地帶,和我們座位地面水平相距有六石級,靠牆處便是四人樂隊了,包括大提琴手,小提琴手,男高音,和女高音。環繞着舞池都是小餐檯,壁上掛滿了風景油畫,古意盎然,侍者先來一杯波蘭伏加酒,驅走了身上的寒氣。於是我有機會悠閒地欣賞那撼人靈魂的歌聲了,似乎都是斯拉夫族的藝術曲Art songs,只有一首調子頗為熟悉,是俄國民歌“漫長的路上”,六零年代美國音樂家改編為流行歌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s。旋律轉速,小鬍子站起來手舞足蹈,最後忍不住拖着妻子,走向舞池。團友中有些老年夫妻亦附和着到舞池去,我想人生遇合是偶然的,我和一部分團友萍水相逢,談得很投契,但相聚期間只是短短十六天。旅程結束後,分遁揚鑣,今生可能再沒有機會見面。我是不會跳舞的,心底下暗唸着晏幾道一首詞:“彩袖殷勤捧玉鐘,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紅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Warsaw Old Town Alley
餐檯上杯盤狼藉,音樂又再升起了。男女歌手站在台前,合唱一首波蘭藝術歌,此歌很長,突然調子轉入了小音階minor mode,樂譜也插進了不少半音符chromatic scale,私家房晚宴中的男女賓客發出了悅耳的和音,是低哼,是吟哦。小鬍子站起來,用雄渾的男中音,和台前的男女高音對唱着。音調幽怨,憂鬱,和私家房內的新婚慶會,大不相稱。很顯然,這首歌在波蘭是家傳戶曉,耳熟能詳的。於是我恍然大悟了,這首歌透露出波蘭的民族創痛,華沙的歷史哀傷。Retmanem餐館的晚飯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一夜,只有在布達佩斯Budapest的吉卜賽音樂晚宴庶幾可近。但此夜激起了民族盛衰,國家興亡的情懷,更刻骨鉻心。
現存世界各國,波蘭歷史是最淒慘,最多斑斑血淚的。波蘭亙古以來是四戰之地,夾在德國和俄國二強鄰間。它們虎視眈眈,擇機而噬,因此波蘭前後共有四次被分割的悲劇,不留下半寸淨土,人民分隸各國,第一次大戰爆發,前波蘭境是東戰場的所在地,波蘭人隨居住地點,被徵入奧,德,或俄行伍,衝鋒時炮鎗相向,同胞互屠,人間慘劇,有甚於此嗎?前三次被奧,普魯士,和俄分割是1773年至1795年,是俄國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 發動的。波蘭人並不是默默甘受宰殺的羔羊,曾有數次反抗,最激動的一次是製鞋匠Jan Killimski率領華沙市民襲擊俄沙皇行宮,在Podwale街頭,矗立着Killimski的銅像,身穿戎服,手持寶劍,義憤填胸,目光如炬,威風凜然,二百年下,猶有生氣。
音樂家蕭邦Ferderic Chopin(1810-49)誕生於華沙近郊的小村,屬俄國。他是音樂天才,六歲作曲,八歲公開鋼琴表演,年青時生活在華沙渡過。1830年負笈維也納,甫離家鄉,便聽到十一月華沙群眾起義抗俄。他滿懷感觸,把那包從華沙帶來的波蘭泥土放在鋼琴上,當晚便譜成了革命練習曲 Revolutionary Etude,此曲先是左手彈出一連串的急速音符,象徵着暴風雨的降臨,然後右手彈出主調,隱喻一聲平地春雷,使局面明朗起來。當然蕭邦對起義軍寄存很大的希冀。不幸地起義軍被血腥鎮壓了,他再沒有機會重歸故土,以後便在巴黎,倫敦,Palma de Majorca,Spain等地過着羈旅流離的生活,獻技謀生。他身居異域,但心懷故國,可惜這國家在他出生前已亡了,作品如降E調鋼琴協奏曲都流露出一絲絲對故國的思慕和哀愁,百多年後聽者也感受到他的音樂感染,對華沙平起了一股親切熾熱的感情。他坎坷的一生,只有和法國女作家喬治辛George Sand相戀期間有過片刻歡娛,最後因健康轉壞而含淚分手。1849年病逝巴黎,遺命姊姊設法將他的心運回華沙。並將一生隨身的波蘭泥土,撒在巴黎墓穴上,以遂他身亡異地,魂返故鄉的宿願。現蕭邦的心存放在一木樽內,隱藏在Krakowskie Przedmiescie大道上的聖十字教堂左殿柱後。我們華沙觀光的其中一站是Royal Lazienki Garden,就在蕭邦那文質彬彬,風度閒雅的紀念像前拍了全體照,彼時滿園秋山紅葉,大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情畫意,據說夏秋二季,每當星期日下午,大草坪上有免費蕭邦音樂演出,遺憾的我行色匆匆,沒有機會欣賞這節目。

Praga
旅遊車再經瀕河大道,越橋抵達Praga區。隔了Vistula河遠眺那華沙老城區,那白牆紅瓦矮矮樓宇,型款各異,犬牙交錯,間有教堂的尖頂,如鶴立雞群,構成一充滿古典色彩的風景線,導遊Ludwig向我們訴說,1944年八月一日Komorowski統帥領導波蘭自強軍,企圖驅逐德國納粹佔軍,展開了六十三天的浴血戰,結果全軍盡墨,都壯烈捐軀了。希特拉盛怒下命令屠城,並向民居縱火,並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我要華沙從此在地圖上消逝。”彼時蘇聯紅軍已開到Praga區,作隔岸觀火,不放一兵一卒渡河,給作困獸鬥的波蘭軍任何紓援,此役華沙市民被殺的超過二十萬,所以老城全部是戰後重建的。Ludwig只有六十歲,面上的皺紋遠超過他的年齡。他是這次大屠殺的餘生者。說此史實時怒形于色,對俄國人恨之入骨。日間看到了Vistula河的滔滔濁浪,這河是華沙飽歷滄桑的見證人,正如中國古都西安有渭水,洛陽,開封有黃河,南京有長江。它們的歷史哀傷,疤痕比華沙多得不可勝數。但華沙創傷猶鮮,似乎將波蘭二百年悲劇擔負起來,充任了近代歷史舞台的要角,我不期然想起了南齊詩人謝眺的名句: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嘆息下心靈感到有點寂寞和茫然。
波蘭第四次被分割是基於1939年八月廿九日希特拉和史太林定的密契,當納粹兵入侵波蘭,炮轟華沙時,紅軍掠取波蘭東部,波軍腹背受敵,首尾不可能兼顧,早注定必亡之勢了。波蘭人和德國人的恩怨遠溯自1226年,Mazovia 侯爵 Konrad請援於日耳曼騎士Teutonic Knights討平東北土著叛亂。這批騎士就在Vistula河出波羅的海Baltic Sea的三角州(即Gdansk附近一帶)安家樂業,後索性鳩佔鵲巢,擴展地盤,建立了東普魯士王國,亦即二十世紀德國軍事搖籃,Gdansk也成德裔城市Danzig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是戰敗國,西普魯士被割歸於重見天日,新獨立的波蘭,成了“波蘭走廊”。Danzig的居民,德裔佔大多數,便成了自由港口,不屬任何國。希特拉第三王國是要包含所有德語系通行地方。Danzig是他志在必得的囊中物。第二次合大戰的戰火是在Danzig燃點起來。華沙被德軍所佔,首先遭殃的是猶太人集居地區Warsaw Ghetto,戰前華沙是國際大城市。猶太人之眾,居歐洲各大城市的首席。從1942年夏起,共有六十萬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遭大屠殺。1943年正月剩餘的六萬激出民變,很迅速被納粹軍撲滅,當場鎗斃了七千,其他送往集中營的煤氣爐內。旅遊車在華沙西北角當年Ghetto舊地巡繞一周,沒有甚麼遺跡可辨,只有廣場中石碑一座,紀念當年的枉死者和龐大的猶太墳場,埋葬了纍纍白骨,此二處聊供後人憑弔罷!

Danzig

華沙老城毀於戰火,倖存的不及十分之一,四零年代重建工作開始了。華沙人很相信邱吉爾名言“不懂得歷史的人一定會遭受到歷史重演的折磨”,小心翼翼地去研究歷史,每一建築物無論在外型,設計,用料,室內佈置各方面盡可能仿古。現在的老城一磚一石,細微處都可以亂真,蔚成世界奇觀。老城入口處是堡壘方場,右邊是王宮,佔很大的面積,中間是高達二十二公尺的石柱,頂端是波蘭王 Sigismund III Vasa (1587-1632),他穿加冕時袞袍,左手持劍,右手執十字架。波蘭曾有過光輝的日子。遠在1386和立陶宛Lithuania結盟組成聯合王國(立陶宛王子娶了波蘭公主),國勢日盛,曾統治烏克蘭Ukraine,治權從波羅的海延展到黑海。此王國持續了四世紀。Sigismund III以瑞典王子入繼大統,影響力波及北歐和俄羅斯。登位後,他將波蘭首都從Krakow遷至華沙。華沙人以此像受着老城大門是有深意的。他們非常緬懷和眷戀昔日的光榮.希望此光榮不是一去不復返,只有此希望,能讓他們忘掉了近三百年的歷史哀傷。
老城有闊大的方場,多為民間藝人用來陳設和出售他們作品處,四週建築物是十七,十八世紀式的,包括三間教堂,但對我最吸引的是北面的華沙歷史館,關於華沙的歷史文獻,搜羅甚豐,每日上午十一時,有華沙被摧毀和重建的記錄片影出。可助我們了解此城在二十世紀的滄桑,從歷史館背後向北行五分鐘是北閘口Barbican,又是一仿古建築物。出了閘口便離開老城了。

Barbican
緊接着老城北閘Barbican是Freta街,有一串矮矮的民房。第十六號是當年居禮夫人Marie Curie (1867-1934)的舊居。夫人的波蘭名字是Manya Sldodowska,出身華沙的科學世家,1890年往巴黎深造,後下嫁物理學家Pierre Curie,夫婦二人合力研究幅射的性能,得1903年諾貝爾物理獎,1906年夫婿病逝,夫人繼續抱其百折不撓精神從事原子工作,發現了新元素,命名Polonium以紀念故國也。1911年因製出元素鐳Radium純質取得諾貝爾化學獎。後半生埋首於X-ray的用途,成效卓著,因長期身體在幅射反應中,激出了血癌,不治去世。波蘭出了三位劃時代的偉人:音樂家蕭邦,科學家居禮夫人,和文學家Joseph Conrad。後者是用英文寫出很多文學小說,這三人的成就有一共通點,都是在外國留下不朽傑作。因為動盪祖國不能供應安定的條件以發揮他們的天才,而他們早成為國際級的大人物,不單止屬波蘭了。

城南近郊Wilanow離宮是保存得最完整的真古跡,是意大利別墅式Italian Villa 的建築,是波蘭王 Jan III Sobieski (1674-96)數年經營的成果。他的軍事才幹高於政治,最喧赫的戰功是1683年在維也納外圍擊敗了土耳其人,使中歐不會淪為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殖民地,保存了奧地利領土的完整,而這奧國就是後來分割波蘭三強之一。奧國統治波蘭人是最開明的,保留波蘭文化,不效普魯士和俄羅斯在波蘭原有土地上分別全面德化和俄化,也許這就是奧國人酬謝昔日解維也納重圍的大恩罷。Sobieski 駕崩後,波蘭王朝國勢急劇下瀉,終於在1795年亡國了。離宮收藏寶物甚多。樓下的宴會廳氣勢堂皇,陳列了很多古老傢俬。樓上有一肖像畫廊,是波蘭各貴族躺在棺材內的遺容。宮外面對意大利花園的牆壁,雕上了希臘神話中專管時間的Chronos。園林樹木蒼翠,置身其間,令人心曠神怡。



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同族不同文,他們染指波蘭的野心在沙皇時代已顯露無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東戰場Smolensk附近的Katyn大森林,紅軍鎗殺了二萬波蘭戰犯,其中有五千名高級軍官。希特拉屠華沙,紅軍袖手旁觀,波蘭精英,全部犧牲於城內,所以戰後波蘭政局呈真空狀態,史太林輕而易舉設立了傀儡政府,將波蘭牢牢關在鐵幕內。共產主義留下很深的烙印,市中心的科學文化宮是一龐然大物,是史太林給波蘭人禮物,被本地人冠以“俄國蛋糕”的綽號。今天有很多華沙人建議將它炸毀,地基變為市中心公園。絕對不易毀掉的倒是華沙外圍一座座灰色像火柴盒般的工人宿舍,構成“三合土森林”。驟然看來和莫斯科,塔什干,烏蘭巴托等外國大同小異,都是共產政權的標誌。看來華沙要擺脫共產主義的污染,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呢。俄國經濟崩潰,很多流氓湧入華沙謀生,扒手,流鶯穿插公共場所中。遊客要步步為營,是華沙一個新污點。

戰後的華沙滿目瘡痍,今日的華沙生氣蓬勃,真是灰燼中的火鳳凰。它內涵豐富,精神雋永,不是我走馬看花式的旅行能探索得盡。讓我抄下沙士比亞的Antony and Cleopatra 其中語粹,為這歷史名城華沙作一總結的寫照罷:
在灰黯的日子中,不要讓我們的悲哀令冷酷的命運竊喜:命運既然來凌辱我們,我們就應該用處之泰然的態度,予以報復。

華沙日落
後記
“華沙蘊藏着歷史哀傷”用沉鬱,蒼涼的筆調去寫那盛衰,興亡。此文涉及波蘭歷史甚多,但不是依事情先後,而是因景生情,兼述及和景物有關的歷史和人物。順便抒發我個人的感概,這是遵守着遊記第四度空間“撫今追昔”和第五度空間“神遊境外”的法則,希望讀者閱來不會有太混亂的感覺。![]()